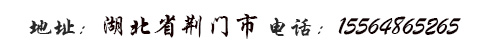遥忆新塍西分部
|
北京痤疮治疗好医院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_9306248.html 文 朱加俊 作者简介:朱加俊,笔名加俊,男,生于年。年加入工人的队伍,工作后有时会练练老祖宗传下来的汉字,在文学的世界里安宁快乐。 西分部是原新塍镇中心小学的一个分部。另外还有东分部,中间有校本部,本部是高年级就读之处,低年级分别就近在两个分部就读。 西分部座落于汲水桥西堍,沿西廊下一条不太长但小路窄窄的如同瓶颈似的,小路走完就到了西分部朝东的大门。 进得校园就显得豁然开朗了,在这闹中取静的地方竟然有这偌大的校园,真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进入大门右边是传达室,传达室后边是后来造的礼堂。在我印象中两幢房子从来没有使用过,只是堆放一些杂物而已。传达室无人传达,一是校园极大多数时间是没有围墙是开放式的,二是人员与经费紧张。 整个校园有十五间教室全部是平房,最好的是进门左手边的独间教室,教室呈手枪型,那转角的小间用以存放教具,教室地面是铺着木地板的,在寒冷的冬天里感觉有一丝温暖感。 有温暖感的不止这一间,中间靠南的两连间教室,在当时堪称是标准化的教室,有宽阔的走廊,教室里面还拉了平顶且刷的雪白,冬天保温夏天隔热,南边是操场视野开阔,其它的教室就稍逊一筹了。 最长的一溜教室有五间,处于校园北端正中间,背靠周家厅一带的民居围墙,长长的走廊在我们儿童眼里显得格外长,西面是简陋的旱厕再往西就是没有门的西门。东端第一间教室是教师办公室并兼有传达室的功能,因离校门较近所以就兼顾一下。 那时候整个校园还没有通电,走廊的梁上挂着一口比足球略大的铜钟,铜钟中间有个鸡蛋大小的活络铜锤系着绳子,上下课全靠没轮到课的老师敲钟。那悠扬悦耳的钟声其实比后来的电铃好听多了。 钟声听久了也能从声音中辩别敲钟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女老师一般敲得节奏慢一些,其余音绕梁能延续一小段时间,男老师敲得就比较急促,上课的钟声就更急了像连珠炮似的,催促着贪玩的男生到教室里。 这钟声一直敲到校园里通了电为止,这时大约在六十年代后期,随着新生的减少教室有了多余,为解决部分教工住房困难,有三户教工家庭住在多余的教室里,由此西分部终于通上了电,有教工家庭的入住,学校放假时顽童们进来玩耍也忌惮三分不敢造次,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照看没围墙的校园的目的,真是一举两得! 其实西分部不是与生俱来的开放式,曾经有过三次围栏,第一次是泥板墙,倒塌后改成竹篱笆,再后来是铁丝网。每一种措施存在时间都不长,原因也多方面的。 首先,放学时大几百人,跻在那羊肠小道般的西廊下,下雨天情况更严重;再则,紧邻校园西侧的孙家浜村民要到陆家桥集市需要走两条直角边,享受不到走斜边的便捷;还有生产队里的几头耕牛总是牛视耽耽地盯着操场中间绿茵茵的嫩草,在牧童的牵引下见空子就钻,跑进来大快朵颐饱餐一顿,那头黄牛偶尔还哞地发出一声牛吼,引得上课的学生哄堂大笑,也算在较严肃的课堂上让师生们短暂轻松一下。 在牛与村民以及家住镇西学生的共同合力下,围栏总是从小洞到大洞再到废弃,再后来校园围栏之事就不再提起,索性开放到底。 没有了围栏上学与放学就便捷多了,由于家就在校园西边仅隔着几十米的郭厅白场,于是上学总是听钟声才去,课间休息也会时不时回家转转。 时间一长难免有主意力分散沒听见钟声的情况,蓦然想起急急忙忙去教室,从教室后门躬着腰蹑手蹑脚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此时我的心怦怦乱跳就像《最后一课》中的小弗朗茨害怕老师严厉的责罚。 所幸教我的老师不是韩麦尔先生,手里也没有戒尺。虽没有皮肉之苦但批评还是少不了的,再屡教不改的话要被记入成绩报告单中的评语。前后有两位美女班主任老师教我们班,一、二年级是徐红鹰(音)老师,三、四年级是许柏荣老师。 尽管两位美女老师兢兢业业地施教,但作为准学渣的我在西分部的四年时光里,一直在升留级线上挣扎着,每当六月份来临在父母的督促下,也有面子观念和虚荣心在作祟,终于开始临时抱佛脚了,与此同时还不忘和差不多成绩的同学玩起了升留级游戏,两个人轮流捏着对方的手臂,用手指篐着手臂两手交替向上捏,嘴里念念有词升级留级……,直到最上端,心中默默地祈祷着不要留级! 经过一个月的冲刺有惊无险地免强跻进升级的行列,不然的话回家的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还要父母多付出二个学期的学杂费与代管费。现在想想有点对不起父母的苦口婆心与两位老师的谆谆教导,她们两位的印象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印象深刻的老师还有新分配来的体育老师沈惠清,生得浓眉大眼中等身材,带几分似凶非凶很严肃的面相,有着发达的肌肉与略显古铜色的皮肤,一看就是教体育的好把式。果然沈老师上起课来有板有眼,操一口稍带嘉善口音的普通话教授运动要领,一招一式总是自己先做示范动作,在沈老师亲力亲为的指导下,同学们从有点怕他到渐渐地爱上了沈老师教的体育课。 那时候主要的运动是不用花什么钱的田径项目,球类运动是无法开展的,因为校园两面傍河,西面与水稻田相邻,若打篮球、排球或踢足球一不小心就会到水里去到稻田里去了,再说学校经费紧张也买不起。 当时跑道上连煤渣也没铺,更遑论今天的塑胶跑道了,那时候连听都没听过! 由沈老师主导的田径运动会不仅中规中矩按标准开展各项比赛,而且破天荒的在运动会期间对喝开水的杯子进行消毒,三个脸盆盛满清水,其中一个里面放了高锰酸钾,水呈玫瑰红。 前一位同学喝好水杯子就浸泡在红色溶液中,后一位同学要喝就拿起杯依次在两个清水盆里漂洗一下,避免了一些疾病相互感染。由科班出身的沈老师教体育也是一件幸事。 体育课能吸引同学们的兴趣和提高身体素质,同样,音乐课也能陶冶情操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只是当时的歌曲都是以唱赞美歌为最主要的,唱得太多了反而记不起来了,抒发感情贴近生活与适宜少儿的歌曲如同凤毛麟角。 印象中有二首儿童歌曲记忆较深,一首是《美丽的哈瓦那》另一首是《我的祖国在黑非洲》,时至今日还能哼上几句,“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西方来的强盗们骑在我们的脖上头………”! 体育和音乐课能给学生带来快乐,当然有快乐就有被管束的难受。那时有一种职务叫做“宣教岗”(音: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由班干部组成,专司纪律检查。主要查看有没有不午睡过早到校或是在街上闲逛又或是在捉鱼摸虾,被逮住了是要汇报班主任的,因此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呆在家里,很少发生被发现的糗事。 但糗事还是发生过一桩较大的,在一个初秋的晴朗天,烈日高照,镇上烟糖公司在郭厅白场晒黑枣,偌大的白场几乎铺满了乌黑发亮的黑枣,在烈日照射下发出阵阵浓烈的香味,向四处弥漫。 两边各有一个工人在油布遮阳伞下照看着黑枣,不过黑枣从晒枣人肩上往下倒时,免不了有些弹到水泥白场外面的泥地上草丛中,这些枣其实枣主人也不要了。有些学生就在泥地上寻找几颗回家喂养风靡一时的廉价宠物——洋虫,当然,不排除挡不住枣香的诱惑吃个一、二颗的情况也是有的。 不知哪位好事者去告诉学校老师说有些学生偷枣子,下午上学各教室气氛凝重,沾上一个偷字的事情不可谓不大。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学校派出老师去了解情况,回来后泛泛地批评教育几句,事情也算平息了。好在哪时十年浩劫没有开始,所以没有上纲上线,这件糗事终告落幕。 下午放学回家时,郭厅白场晒枣人早已打道回府了,白色的水泥场地上还星星点点地遗留一些黑枣,爷爷奶奶辈的人在捡拾,而路过的学生再也不敢捡拾了。(顺便科普一下,黑枣不是枣,属柿科与柿子是亲戚,与枣没半毛钱的关系,只是形似枣自古以来叫惯了而已。) 通过西分部四年的学习,我由儿童成长为少年,四年里有响亮悦耳的钟声、琅琅上口的文章朗读声;也有愉快的歌声与此起彼伏的运动会上的呐喊助威声相陪伴,当然作为准学渣的我,时不时有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刷刷存在感,还有被批评的声音少不了在耳边回荡。现在想想童年时光既快乐也有后悔。 六五年秋进入校本部学习,一个半学期后的六六年春十年动乱开始了,学校停课两年多,全部学生都辍学在家,等到六八年秋复课了直接进新塍中学读初一。因此,校本部的记忆远不如西分部深刻!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离开西分部已近一甲子,西分部的地块随着时光的进展也发生了沧桑之变。学校办到七四年底,七五年开通人民西路,西分部靠北面小部份被拆成了马路,其余的归了房管所和房修队,西面的稻田造起了电影院,目前尚在只是不再放电影了。 转眼到了新世纪,此地块被出让给开发商建造了商品房,孙家浜村民搬迁到农民新村。唯一不变的是傍着校园东南两面的两条小河还在,日夜不停地在静静流淌,仿佛在无言地诉说着西分部的往事! 人上了年纪后乡愁与怀念往事的情结愈发强烈,回不去的是年龄,但思念与情怀可以飞回到童年,为此挥就绌文一篇与西分部及新塍镇中心小学(现名:磻溪小学)的校友们共忆快乐的儿童时代!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jp/10606.html
- 上一篇文章: 里三国外三国俄土伊三国在南高加索冲突中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