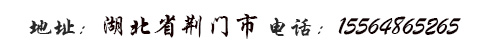飓风掠过蔗田摘抄04
|
c#.net开发求职招聘微信群 http://www.cgia.cn/news/chanye/1663791.html第七章和美国总统同游哈瓦那 灰蓝色的天空中浮现出架飞机的剪影。起先只是从厚实乌云中穿出的一个黑点,但越变越大,如同润开的墨滴。人们屏住呼吸,用一种察看孕期超声照片的神情注视着它。 突然间,又有一架飞机出现。现场立即被一种沉默的尴尬笼罩着。 我总会在完成天的工作后去那里喝一杯。黄昏时分,夕阳像一块块金纱盖在四周建筑的顶端,特别是东南角一座塔楼,虽然已经是断壁残垣,但在光线的反射下闪烁着一种无论多么高超的人工都打造不出的色泽。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年少时在马德里求学的夏天,那些在夜幕降临后步行横穿马约尔广场的时光。这是建筑蜕变和人心成长之间互相映射、产生共振的最好例证。 古巴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多一座圣胡安或者巴拿马城。在这些曾经是殖民重镇的老城区,为游客修缮新的花花绿绿的殖民街道和喷泉广场如同一块口香糖,最初的那几下咀嚼香味四溢,但很快就变成味如嚼蜡的一嘴黏渣。 几来远的地方,修路工人正在凿洞埋线,整个路面都震动起来。我们头顶的宣传画的确像是面镜子。 黄昏时分,工人们还在微散发省热气崭新西青路面上画出白色的交通标线。我赶到自由哈瓦那酒店给东半球的晨间新闻做视频连线。欧广联在酒店的高层长期租货了,一个办公室,其实就是个高级套间,原来摆放着沙发茶几的客厅塞满了工作台和直播的设备,连接着阳台的卧室被改造成演播室,粗细各异的线缆在米色的地毯上匍匐爬行。只有宽敞的浴室能够透露这个空间的真实身份,它没有被改动过,一迈进去就又回到了酒店的气氛中。 热爱建筑的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莫鲁齐在他的图文集《卡斯特罗前的哈瓦那:当古巴是一座热带乐园》里说,巴蒂斯塔将这个酒店视为自己最骄傲的成就之一,因为它像一块巨大的吸金石,不但能引来大手大脚的美国游客,更会让对岸的资本家们从众跟风,毕竟谁敢质疑希尔顿家族的投资眼光。 然而哈瓦那希尔顿酒店如同福过灾生的泰坦尼克号,处女航就撞上了革命的冰山。在它迎来的第一个新年夜,得知圣地亚哥已经失守的巴蒂斯塔正焦头烂额地准备逃离古巴的行装,酒店里觥筹交错的跨年派对倒像是沉船前的乐队演奏。 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当年的苏联人,他们在海最阳台上凭栏俯瞰的最致和我此刻所见应该是一一样的吧。连线开始前半小时,欧广联的工作人员开始给我试光。调试间歇,我转过头向外看,仿佛被眼前的光景击中一般。海面蓝得发亮,它与海堤的交界线仿佛被一把锋利的刻刀仔细雕刻过,每一道皱褶都清晰得如同用放大镜照过似的。真正发挥魔力的其实是西边射来的霞光,它把矗立在海滨大道边的每一栋建筑都照亮了,又把每一个背光的位置都仔细藏好。这种近似造物者的视角很容易让人忽略掉这片土地上的政权更迭的过往和交纵的悲欢,它化成了只有在地图中才具有意义的线条,我甚至能看见第一批欧洲航海家的船只正在向岸边驶来。 很快,仿佛自动加上了一层滤光镜,视野变得愈加柔和,城市上空飘散着轻薄的金光,远处的莫罗城堡仿佛海岸线上一颗白色的图钉。光影随时都在变化。 然而在这个晨昏之交,海滨大道的路灯早早就亮起来了,似乎比平日里更加耀眼。连线开始前的几分钟里,天色以一种无法阻挡的态势暗了下来。透过挂在天花板的实时屏幕,我发觉身后的哈瓦那已经笼罩在蓝紫色的倦意中。平静的海面像是一把刺向城市的弯刀,闪烁着粼粼的寒光。 “我种一朵白玫瑰花,七月好月也不差,为了那真心的朋友。”戴着牙套的鬈发少女坐在海滨大道的石堤上。 “她头戴斗牛士的帽子,和他的绯红色斗篷,仿佛戴着帽子的垂悬的紫罗兰。”短发的中年女子是一所小学的年级辅导员,她刚敲过下课铃。 “别把我囚禁在黑暗中,那是叛徒的死法。我是正直的,如此正直,要面朝太阳死去。”在塞斯佩德斯公园的长椅上,满头白发,却又看不出年纪的古巴男子一边背诗,一边挥舞着右手。 台阶的尽头就是马蒂的全身像,他屈腿坐着,手臂放在膝盖上。每一次从革命广场向上仰望,我总辨别不出马蒂的视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他都略带愠怒地瞪着在他脚边徘徊的人。 革命宫的上空乌云密布,为总统们准备的红毯犹如一条猩红色的巨舌。记者会结束后我特意上去踩了一脚,地毯是干的,雨始终没有再下。 让我颇为意外的是,记者们都年轻极了,有几个相貌姣好得如同电影演员,仿佛写稿只是片场闲暇时的消遣罢了。 广告自带的地图上,轮船的航线被画成一个直角,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只是为了凸显当年美古货运业务的快捷和便利。 在这座革命的岛屿,新闻还未见报就已经旧了。太多的段落似曾相识,再激动人心的消息都很难用句号结尾。我仿佛能听见午夜时分印厂车间里传出的轰鸣声响,犹如黑暗中的句句复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jp/12532.html
- 上一篇文章: 古巴找到坠毁波音737客机第二只黑匣子
- 下一篇文章: 餐桌上的古巴海盗殖民革命之后的饮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