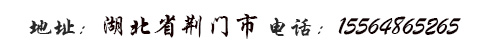窃格瓦拉是对格瓦拉革命反叛精神的一
|
山东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xwdt/151016/4710759.html 恩内斯托·切·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作为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具感召力的形象之一,曾经激起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热情。当下的年轻人又是如何认识切·格瓦拉的呢?或许是四处可见的印有格瓦拉形象的T恤、打火机或者香烟盒。切·格瓦拉形象的商业化流行,似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就已经开展。但是,切·格瓦拉的形象却因此走向全面的商业化和扁平化。而当今“窃·格瓦拉”的流行,到底是一种对严肃的彻底消解,还是在后现代意义下的消极反抗?如果其中有反抗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是切·格瓦拉?这其中反映了年轻人对格瓦拉怎样的理解与想象? 在取消了对历史全面、深度了解的今天,我们要怎样才可能穿越历史的地平线,去寻找真正的切·格瓦拉,去感知全球六十年代激昂的历史?在西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整个西方世界以民粹主义为首的右翼思想正在抬头,重提切·格瓦拉的国际主义精神又有怎样的意义?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未来潜藏于历史之中,我们只有重新叩访历史,才有可能找到当下危机的答案。我们需要召唤回切·格瓦拉的“幽灵”。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切·格瓦拉著,郭昌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8月出版 近日,切·格瓦拉所写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全新译本出版,新京报专访此书译者郭昌晖,和他探讨关于切·格瓦拉的经历与思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以及如何在今日世界重新开启切·格瓦拉的精神遗产。 郭昌晖,年生,青少年时期在沪求学至高三毕业后学业戛然中断。下乡十载,年再进学堂。毕业后在北京高校教授英语,年退休,教书匠从一而终。翻译是教书之余之爱好,曾受聘为商务印书馆《英语世界》杂志特邀译者。 切·格瓦拉凸显了一个大无畏的反叛形象 新京报:注意到你之前翻译过切·格瓦拉的另一本著作《玻利维亚日记》,为什么选择翻译切·格瓦拉?在你的生命经验中,你是如何与切·格瓦拉相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驱使着你去翻译切·格瓦拉? 郭昌晖:实话实说,译此书并非我的自主选择。出版社邀我译书,我没有婉拒译格瓦拉,是因为格瓦拉是一个例外——古巴革命胜利后,他本可以躺在权力的宝座上享受,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抛弃斗争得来的一切,重新回到原始的丛林,直至遭敌人杀害。格瓦拉为什么就这么特殊? 我第一次与古巴有“瓜葛”,还是幼时在游行队伍里高呼“古巴西,扬基诺”(“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五十多年后,我表面是在译有关古巴的书,心里翻腾的却一直是有关当下的问题。 切·格瓦拉 新京报:美国学者詹明信认为全球六十年代开启于年元旦古巴革命胜利,在你看来,古巴革命战争之于六十年代,甚至之于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为何重要?而切·格瓦拉之于六十年代的意义何在?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切·格瓦拉的形象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郭昌晖: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的基本格调是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统治,反帝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掀起高潮,到处弥漫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谋求平等正义的“乌托邦”的时代精神。仅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独立,所以年也被称为“非洲独立年”。 古巴革命其实就是这些新兴国家崛起的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但不同的是,它紧邻美国,让美国感到东方阵营威胁到了自己。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开始渗透至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从地缘政治看,这自然对美国形成巨大威胁。 施莱辛格曾说:“革命的古巴有一股在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找不到的不顾你死我活和无法无天的热情。”他们担心的不仅是一个古巴,而是在北美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都对古巴革命寄予信任,怀有希望,担心打破当时暂时的美苏平衡状态。 所以,古巴革命胜利初期,美国就策动了猪湾事件。赫鲁晓夫于年又趁机利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引发了一场险些毁灭世界的危机。这一切都将古巴革命推向了东西方两大集团争斗的世界动荡的漩涡,成了全球瞩目的中心。 在这场斗争中,格瓦拉凸显了一个既强烈反美,又不愿依附苏联的大无畏的反叛形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动荡不仅表现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也表现在东西方两个阵营都不安生。格瓦拉的形象成了西方动乱——巴黎的“五月风暴”,伦敦的动荡,美国的反越战浪潮——的催化剂。 这种影响的深入和持久性非常令我震撼。自年出走古巴,他试图把古巴的革命火种带往拉美后,便真正开始履行自己信仰的国际主义义务,美国唯恐拉美这座美国的后院被这位全球的叛逆者点燃起造反的烈火,动摇其对拉美的控制和掠夺,便动用了中情局的力量,配合玻利维亚政府当局对格瓦拉的游击队进行围剿,直至最后将其杀害。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也为格瓦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起到了最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格瓦拉的传奇地位从此开始形成。年《时代》周刊评选格瓦拉为二十世纪“世界偶像”之一,而且是高票当选。他的反美的国际主义斗士的形象就此确立。此后的世界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充满火药味,格瓦拉也渐成一种流行的符号被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起来,但他却始终是青年人心中的偶像,不管对他的一生是否有所了解,反正可以对他进行无限的解读。 切·格瓦拉的国际主义行动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所趋 新京报:在切·格瓦拉短暂而又辉煌的生命中,从环游拉丁美洲,到参与革命战争,最后前往玻利维亚作战,他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郭昌晖:格瓦拉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人,这种难以更改的性格上的遗传从小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小时候虽有哮喘病的他,非参加最激烈的体育活动不可。学医期间便与朋友一起骑着摩托车开始了他们的南美洲之行,这一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由于穿梭在最底层的民众中,自然对他良心是个极大的触动,他看到了民众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对大多数穷苦人逐渐萌生出怜悯和同情。与一般青年从书本上获得的体验相比,格瓦拉的情感显然更加刻骨铭心,他曾说:要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凭天主教堂、当地的神庙、博物馆甚至什么圣母显灵地,这些只是最表象的东西。在医院里的病人、监狱里的犯人或是忧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会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真正灵魂。这种人道的关怀没有与底层民众的鱼水一样的接触是不会生成的。 格瓦拉思想的逐步升华和他在旅行中亲身参与民众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与各国共产党人的接触是分不开的。在智利的铜矿,在秘鲁的麻风病院他不仅为民众治病,还参与他们的斗争,在斗争中他经常与共产党人交谈,逐渐使自己的人生目标与民众的苦难融为一炉。 格瓦拉在危地马拉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目睹了美国中情局勾结危地马拉军人集团发动政变、颠覆了总统阿本斯的政权后,他确信进行武装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他当时的悲痛心情使他“和所有的危地马拉人站在了一起,希望为痛苦不堪的国家摸索出重建未来的道路”。 他越来越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ly/11081.html
- 上一篇文章: 第二期出炉,穿搭之外更多了对宜居
- 下一篇文章: 第13届哈瓦那双年展中国单元作品完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