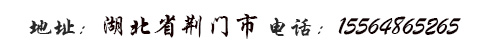卡尔维诺我最害怕的是重复自己
|
点击上面↑↑↑蓝色字免费订阅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年10月15日出生于哈瓦那的郊区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他父亲马里奥是个农艺学家,在热带国家度过了许多年,主要是在拉丁美洲。卡尔维诺的母亲伊娃是撒丁岛本地人,也是个科学家,一个植物学家。他们的儿子出生后不久,卡尔维诺一家便回到了意大利,定居在卡尔维诺教授的老家利古里亚区。当卡尔维诺长大成人,他的时间一部分是在圣雷莫的海边小镇度过,他父亲在那里管理着一个花卉栽培试验站,一部分是在山里的乡村宅邸中度过,小卡尔维诺在那里开荒种树,栽种了一些柚子树和鳄梨树。这位未来的作家在圣雷莫上学念书,然后在都灵大学的农艺系登记入学,在那里只坚持到了第一次考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人占领利古里亚区及意大利北部其余地区时,卡尔维诺和1岁的弟弟逃避了法西斯党的征兵,加入了游击队。后来,卡尔维诺开始写作,主要是写他的战时经历。他发表了最早的几个短篇小说,同时重新开始大学的学业,从农艺转到了文学。在这段时期,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通往蜘蛛巢的小径》,他把这部作品递交给了蒙达多里出版公司赞助的一次竞赛。小说没有拿去参赛,但作家切萨雷·帕韦泽把它转交给了都灵出版商朱利奥·伊诺第,后者接受了这部小说,并和卡尔维诺建立了将持续他大半辈子的关系。当《通往蜘蛛巢的小径》在年——也就是卡尔维诺拿到大学学位的那一年——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为伊诺第工作了。在战后时期,意大利文学界深深地卷入到了政治,而都灵,一座工业之都,则是焦点。卡尔维诺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为该党的日报写关于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报道。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卡尔维诺尝试了几次写第二部长篇,但直到年,也就是5年之后,他才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在埃利奥·维托里尼的资助下,这本书放在被称作“象征主义者”的新潮作家们创作的一套丛书中出版,立即受到了评论家们的赞扬,尽管它违背了第一部小说那种更现实主义的风格,并导致来自本党的批评,年,当苏联入侵匈牙利时,他便退党了。年,卡尔维诺出版了一部开创性的《意大利童话集》。次年,他出版了《树上的男爵》,9年出版了《不存在的骑士》。这两部小说,连同《分成两半的子爵》,被收集在《我们的祖先》这本书中。年,他出版了《宇宙连环图》,年,他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反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出版。他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帕洛玛先生》()和短篇小说集《困难的爱》()。年9月19日,在罹患中风13年之后,卡尔维医院里去世。我第一次遇到伊塔洛·卡尔维诺是在罗马的一家书店里,那是年春天的某个时候——我记忆中的画面里我们都穿着单薄的西装。过去十多年里我一直生活在罗马。卡尔维诺只是不久前,在巴黎待过很长一段时期之后,才回到这座城市。他唐突地问我——他从来不是一个说话拐弯抹角的人——我愿不愿意翻译他最近的一本书《宇宙连环图》。尽管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我立即说没问题。离开书店前我拿起了一本,我们约好几天后聚一下。他和家人一起住在这座城市中世纪街区一幢很小的、最近才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公寓里,紧挨着台伯河。像我稍后将会展示的卡尔维诺的宅邸一样,这套公寓也给人以陈设简朴的印象;我记得光秃秃的白墙壁,大量涌入的阳光。我们谈论了这本书,我已经在此期间读过了。我得知,他已经试用过——并解雇了——一个英文译者,我想知道我的同事被解雇的理由。卡尔维诺有欠慎重地把通信拿给我看了。这本书里有一个短篇小说题为《没有颜色》。译者很不明智地想来点独创性,把这篇小说的标题翻译为“黑白之间”。卡尔维诺的辞退信指出,黑和白都是颜色。我签下了合同。我第一次翻译卡尔维诺有一段艰难的历史。就在我快要完成的时候,委托这项任务的美国编辑换了工作,而且——听从我不幸的建议——卡尔维诺也跟着他转到了他的新公司。但接下来,那位编辑自杀了,新公司拒绝了《宇宙连环图》,老公司不愿让我们回去,这本书于是便四处漂泊。另外几个出版商拒绝了它,直到最后,HarcourtBraceJovanovich出版公司的海伦·沃尔夫接受了它,开始了卡尔维诺与这家出版公司的漫长合作。这本书受到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不难想见,一次猛烈的批评来自第一个译者),并赢得了国家图书奖的翻译奖。从19年直至他去世,几乎很少有哪段时间我不是在翻译(或者被认为在翻译)他的某件作品。偶尔,他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几页文字——他要为加拿大的一个电视节目发表的一份声明,或者他给一本论述管道系统的书写的简短导言。他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任务:令人惊叹的《命运交叉的城堡》()是作为一篇评注而诞生的,评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副塔罗牌。在卡尔维诺那里,每个单词都要反复推敲。我会对最简单的词犹豫整整几分钟——bello(美丽的)或cattivo(坏的)。每个词都要试。当我翻译《看不见的城市》时,我在乡下的周末客人总是被迫听我大声朗读一两段译文。作家未必都很爱护他们的译者,我偶尔感觉到,卡尔维诺更愿意自己动手翻译他的作品。在后来那些年里,他很喜欢看译稿的长条校样;他会做一些改动——用他的英语。这些改动未必是对译文的改正;更经常的情况是修改,是改动他自己的文字。卡尔维诺的英语更多地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符合语言习惯的。他还有一个习惯:总是爱上外语单词。在《帕洛玛先生》的译文那里,他发展出了对feedback(反馈)这个单词的迷恋。他不断把这个单词插入到文本中,我总是巧妙地把它拿掉。我不能清楚地向他表明,像charisma(魔力)、input(输入)和bottomline(底线)一样,feedback这个单词,不管在意大利人的耳朵里听上去多么漂亮,但它不适合出现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驱车去卡尔维诺的避暑别墅——那是一幢现代化的宽敞别墅,位于格罗塞托省北部托斯卡纳海岸罗凯马尔一个僻静的住宅区。在互致问候之后,我们在宽敞荫凉的露台上舒适的大椅子里坐了下来。看不见大海,但你可以通过辛辣而芬芳的空气感受到它。卡尔维诺大多数时候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从来都不是特别随和。他总是去见一些相同的老朋友,其中有些人是伊诺第出版公司的同事。尽管我们彼此认识已经20年,互相去过对方的家里,一起工作过,但我们从来都不是无话不谈的心腹知己。实际上,我们互相用正式的lei(您)称呼对方;我称他卡尔维诺先生,他称我韦弗,不知道我多么痛恨别人用姓氏称呼我,总是让我想起私立学校里担惊受怕的时光。即使在我们直呼其名之后,当他给我打电话时,我也能感觉到他在说出“比尔吗?”之前那片刻的暂停。他很想像过去一样叫我韦弗。我不想给人留下他不友好的印象。连同他的沉默寡言一起,我还记得他的大笑,在我们一起工作是经常由于某件事而触发。我还记得他送给我的礼物,一份精美雅致的小出版物,关于洛伦佐·洛托最近修复的一幅画《圣杰罗姆》。在书里,卡尔维诺写道:“送给比尔,像圣徒一样的翻译家。”回想此事,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像个闯入者。采访者在你工作期间,谵妄——如果有的话——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卡尔维诺谵妄?……我试着回答吧,我一直很理智。不管我说什么或写什么,一切都服从于理性、清晰和逻辑。你会怎么看我?你是不是认为,当我提到自己时我完全瞎了,有点偏执狂。另一方面,如果我要回答的话,哦,是的,我确实有点谵妄,我写作的时候总是仿佛自己处在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我不知道怎么写出这样疯狂的东西,你会认为我是个骗子,在扮演一个不太可信的人物。或许,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我把自己的什么东西放进了我所写的东西中。我的回答是——我放进了我的理性,我的意志,我的品味,我所属于的文化,但与此同时,应该说,我控制不了我的神经质,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谵妄。采访者你的梦是什么性质?你是不是对荣格比对弗洛伊德更感兴趣?卡尔维诺有一次,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之后,我上床睡觉了。我做了梦。第二天早晨,我能够清清楚楚地记起我的梦,因此我能够把弗洛伊德的方法应用于我的梦,并非常详细地解释它。那一刻,我相信,对我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从那一刻起,我的梦就不再对我保守任何秘密了。此事并未发生。那是惟一一次,弗洛伊德照亮了我的潜意识中的黑暗。打那以后,我就继续像以前那样做梦。但我忘了它们,或者说,就算我能够记起它们,我也丝毫理解不了它们。解释我的梦的性质,既不能让一个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家满意,也不能让一个荣格学派的分析家满意。我之所以阅读弗洛伊德,是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一个惊悚警匪片的作家,读起来很有激情。我也读荣格,他感兴趣的东西对一个作家来说很有意义,诸如符号和神话之类。荣格不是一个像弗洛伊德那样优秀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们两个都感兴趣。采访者命运和机遇的形象十分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小说中,从塔罗牌的洗牌,到手稿的随机分发。机遇的观念是不是在你的创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卡尔维诺我那本塔罗牌的书《命运交叉的城堡》是我写过的所有作品中算计最清楚的书。没有给机遇留下任何东西。我不相信机遇在我的作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采访者你是如何写作的?你如何进行写作这一身体行动?卡尔维诺我用手写,做很多很多修改。我会说,我划掉的比我写下的更多。当我说话时,我不得不字斟句酌,写作时我有同样的困难。有些时候,我自己都认不出我的笔迹,因此我使用一个放大镜,以便弄明白我写的是什么。我有两种不同的笔迹。一种写得很大,字母相当大——o和a的中间都有一个大洞。这是我在誊抄或者当我对自己正在些什么颇有把握时的笔迹。我的其他笔迹对应于不那么自信的精神状态,字很小——o就像小圆点。这样的笔迹很难辨认,即便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我的稿纸上总是布满了删除线和修订。有一段时期,我制造了大量的手写稿。现在,在完成第一稿(手写的,涂得乱七八糟)之后,我开始一边破译,一边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当我最后重读手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本,我经常要做进一步的修订。然后,我做了更多地修改。在每一页上,我首先试着用打字机进行修改;然后我用手做更多的修改。经常,稿纸变得无法辨认,我不得不把它再打一遍。我很羡慕那些不用修改、一气呵成的作家。采访者你每天都工作,还只是在某些日子、某段时间工作?卡尔维诺理论上,我很想每天都工作。但在上午,我总是编造各种可能的借口不工作:我要外出,要购物,要买报纸,等等。通常,我总是设法把上午的时间浪费掉,因此,我最后总是在下午才坐下来写作。我是一个白天的写作者,但由于我浪费了上午的时间,我也就成了一个下午的写作者。我晚上也能写,但当我晚上写的时候,我就不睡觉了。因此我试着避免这样。采访者你是不是始终有一系列的任务,有你决定要着手的具体事情?或者,你是不是同时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进行?卡尔维诺我始终有很多计划。我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我想写的大约20本书,但事到临头,我决定我要写那本书。我只是偶尔才是个长篇小说家。我的很多书是由一些集在一起的简短文字所组成的,短篇小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它们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书。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结构一本书,列出一些最后证明对我来说毫无用处的提纲。我把它们都扔掉了。决定这本书的是写,是实际呈现稿纸上的材料。我开头总是很慢。如果我有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我总是找出各种能够想到的借口不去着手写它。如果我要写一本短篇小说集,短文集,每一篇都有自己的起始时间。即便是文章,我开头也很慢。即便是给报纸写的文章,每一次着手动笔我都要遇到同样的麻烦。一旦动了笔,接下来我就可以写得很快了。换句话说,我写得很快,但我有大段的空白期。这有点像那位伟大的中国艺术家*的故事——皇帝叫他画一只螃蟹,艺术家答道,我需要10年时间,还要一幢大房子,以及20个仆人。十年过去,皇帝找他要那幅螃蟹。他说我还需要两年。接下来,他有要求延期一周。最后,他拿起画笔,大笔迅速一挥,片刻间画出了那只螃蟹。采访者你是从一小组互不相关的想法开始,还是从一个你逐步填充的更大的概念开始?卡尔维诺我从一个很小的、单一的意象开始,然后我把它扩大。采访者屠格涅夫说:“我宁愿要太少的结构而不是太多,因为那样会干扰我所说出的真相。”你能不能就自己的写作评论一下这个说法?卡尔维诺有一点倒是真的,在过去,就说过去十年吧,我的书的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或许太重要了。但是,只有当我觉得我已经实现了一个严密的结构,我才相信,我已经有了自己站得住脚的东西,一部完整的作品。例如,当我开始写《看不见的城市》时,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关于框架是什么,书的结构是什么。但接下来,一点一点地,设计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支撑了整本书;它成了一本没有情节的书的情节。对于《命运交叉的城堡》,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结构就是书本身。到那个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痴迷于结构的程度,以至于我几乎为之而着迷。关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可以说,如果没有非常精确的、铰接非常严密的结构,它就不可能存在。我相信,我在这方面成功了,它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当然,所有这种努力,读者根本不应该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xj/7286.html
- 上一篇文章: 周末去哪儿原来儋州妹子这么美还有
- 下一篇文章: 从网红家族到金钱帝国,卡斯特罗子孙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