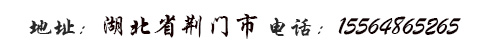郝寒冰散文附小记忆
|
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最专业 http://m.39.net/pf/bdfyy/bjzkbdfyy/ 作者郝寒冰 我新搬的家对面是一所小学,每逢中午,无数的老头老太太就围堵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孙子放学回家,有时人多一拥挤,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我就奇了怪了,好像别的学校门前没有这多人,这个学校是咋回事啊?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胖婆姨见我傻不愣登的,笑着问我:“看样子你是从县里来的吧?”我只好含混的道一声“嗯哪……”——原来如此,我就说嘛,之前没有见过你!胖婆姨说,你不知道吧,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校,这是21小学xx分校,21小学,不知道吧?这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多少人头打破了往里挤都挤不进来,唉,说多了你也不懂!我就想笑,当然是偷着笑,我不懂?你懂?我真想说一声:你真当我是县里来的,啥也不知道?你给我听好了,老姨妈,我可是正经八百的21小学的毕业生,不过那时这所学校并不叫什么21小学,而是银川师范附属小学,简称“银师附小”,俗称“附小”,你知道啵?!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势不可挡——我是年10月走进银师附小校门的。之前,我家在当时的自治区公安厅下属的潮湖农场,就是现在大武口附近的国务院“五七”干校旧址,我在那里的一所“完小”上三年级,随着父亲工作调到了厅机关,我家也搬到了银川,就在附小东墙外。上附小时的我学校位于老城文化街与民族北街坐标点的西北处,正门向南开着,直对文化街,大门两边的白底墙壁上写着红色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显得格外瞩目。西边与“文化大院”为邻,东边紧靠民族北街的是一排青砖墙,北面隔着两排民居就是著名的大湖——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个令后人费猜想的地名“湖滨街”。按照那时就近入学的原则,我们自然而然的应该转到附小上学,无需走什么门路。附小的教导处对我和我哥、我妹三人进行了一下文化测试,出了几道简单的问答题,一个小时交卷。之后研究了一下,认为潮湖“完小”的水平太低,建议让我们仨每人降一级。那个时候学校说啥就听啥,家长也没有意见。所以,我就此被编进了二(1)班。其实对我而言,没有什么降低的意义:因为我原来是普通班三年级的,要上6年学,刚好66年夏毕业,现在名义是降了一级,但因为是五年一贯制,二年级也是66年毕业,等于还是打了个平手。而我哥和我妹就真是掉了一个台阶。如此一来,严格的讲,我也算不上是“正宗”的附小学生了——因为按照我的理解,纯正“血统”的“附小学生”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从一年级一直上到毕业的学生,从上学伊始就一天不拉的在这个班里度过的,而我则没有跟大家共同度过一年级的时光,是从2年级才插进来“入伙”的,一开始进入的就是二(1)班,再到三(1)班、四(1)班,直到最后的五(1)班,满打满算只在附小呆了5年不到的时间,但是也相对可以啦,有吹牛的资本了!全银川那时共有16所小学,附小是最好的学校,无论是教师水平、教学设施、教学质量还是学生的总体素质,当时的附小都是第一流的。先说这里的老师。著名学者梅贻琦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实际上一些有名气的中、小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至少在我的眼里,银师附小就是典型一例!年代之初,新中国成立才刚刚10年多一点时间,由于历史原因所致,一大批当年在京津沪干过各种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人员陆续转岗来到宁夏当了支边小学教师,他们的到来,无疑为这方传统上非常闭塞的水土带来新鲜的空气,用现在的话说,“大咖”云集,群星闪烁,想不出名都不行。校长雷德凤,一个中年女性,操着一口带有明显川腔的普通话,外表儒雅随和,说话办事稳当利落,有人传说她是和《红岩》中的江姐一起干革命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不情楚,但很像那么回事。语文特级教师周毓济是周恩来总理的堂妹,来自京城,算术特级教师杨恩光同样来自北京,曾经的上海广播电台播音员林淑肩,曾参加过抗日少战团的胡知侠,毕业于绥宁师范的刘国安,教导处主任何世雄,资深音乐老师张明,来自北京回民学院的马志凤,体育老师朱佩仁和张锡善,政治老师朱生录等等,个个都是人物,敬业精神和教学水平都让人无话可说。甚至连年轻教师也都不是吃干饭之辈。银师附小,顾名思义,是银川师范的附属小学,换言之是师范的教学实验基地,每年毕业实习都在此进行,只有那些最优秀的毕业生才能被附小看中留下,年复一年,形成良性循环,人才辈出。年底,即将开始的大动荡到来之前,最后一批分配到附小的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从中原之地河南省自愿支宁的师范应届毕业生,两男两女:李洪文、吴臣堂、冯婉菊、闫秀梅。比我们大不了多少,长着娃娃脸,所以一直记得他们的面容。我的五届班主任老师来自祖国各地,分别是北京人云正虹老师、陕西人王自宽老师、东北人傅丽萍老师、云南人张启华老师和河北人马志凤老师。他们都极富个性,云老师的活泼浪漫,王老师的朴实稳重,傅老师的慈祥爱心、张老师的冷静沉着,马老师的热情洋溢,都让我看在眼里、学在心里。我一直认为,银师附小之所以60多年丰碑不倒,原因就在于建校伊始奠定的整体基础扎实牢靠,而那些优秀的老师就如同水泥桩一般根根都是过硬的!他们都是那个年代里的佼佼者或者是领衔者,换句话说都是些“人物”——尽管大都40岁左右,但我始终认为他们代表着附小在当时的业务和学术水平,与今天同样年龄的小学教师相比,无论是从做人还是做学问哪个角度来衡量,都是有相当差别的。说句可能不太准确的话,把这些有水平的人放在一所小学教书于国家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对学生而言,又是一种奢侈,当然,也是我们的有幸。可惜的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知挥霍,不知汲取,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借用陆游的原话“一杯愁绪,几年理索,错!错!错!”来形容恰到好处!年代作者笔下的附小但是,我们毕竟是这些优秀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特别有幸的时我们恰恰是在WG前告别小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命”非常好,因为我们好歹算是受到“正规教育”的小学生,要比那些后十年上小学的孩子们侥幸的多得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若干年后在银川、宁夏甚至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一些人物都毕业于这里。远的就不说了,光我看到的65级、66级毕业生中,就产生了2位省级干部,50余名厅级干部,以及一批知名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社会贤达,也鲜有听说当年附小的哪个同学“进去了”的消息。恐怕正是因为具有如此美好的教学质量、人脉关系和地理位置优势,所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附小始终没有搬迁,虽然学校名字不断在变化着,但就是到了今天,“21小学”仍然是全市人民心中不倒的“克里姆林宫”,大家依然以把自己的孩子能够送进这所学校为荣!那时的校园也真大,一进大门迎面就是一座呈大写“亚”字型的青砖坡顶小洋房,建造在接近一米高的台阶上,非常有气势,房间也很多: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两边分别是校长办公室、教导处、教研室、图书室、广播室。学校共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各有四个班,青砖红瓦形状的教室分为东西两列,每列四排,每排四个班。东半拉教室的前面是小足球场,西半拉教室的前面安装着单、双杠、转椅、压压板、天梯、巨人步等运动器材。教室的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有米跑道,还高高矗立着一架在当时非常罕见的大型运动器材——“五部联合器”,装有秋千、吊环、云梯、铁杆、爬绳。西北角两排平房是教职工家属院。除此之外,还有开水房,烧火的是一个姓哈的师傅,门房的山东籍老头李鸿飞负责收发报纸和打上下课铃,大家都管他叫“老李叔”。因为家近,每天早上我都是最早到校的学生之一,当然,就是家远,我也会提前到的,因为我已经觉得呆在学校要比在家里有趣。当时天气已经入冬了,那会儿没有暖气,班里生着火炉子,就是那种北京生产的铸铁炉子。班里按照座位的排法分为四个小组,每周各个小组轮流做值日,每天晚上放学的时候压火,第二天早晨再捅开炉子,后来的同学一进教室便感到不仅身上暖哄哄的,而且心里也热乎乎的了!每天上午四节课,主要是语文、算术,中间还要穿插着做体操和视力保健操。我尤其喜欢做视力保健操,因为我特别爱听那个音乐,也不知为什么,听着听着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课间休息期间,男同学在院子里抽老牛、滚铁环、挤暖暖。女生们最爱玩“天梯”,实际上就是一种立式的“压压板”——两个人各自站在中轴的一边,高举双手使劲抓住头顶上悬着的木头把手,然后相互用气发力,“天梯”马上就晃动起来,忽高忽低。为了显示自己的开心,有的女生高高在上的一刹那,还用力把脖子往横杆上抻一下。有一次我正在看着她们玩,就听一个坏怂说“放手放手!”结果恰好刚刚蹲在地下的女同学下意识的一松手,正好把那头跃在天上的女同学给摔到了地下,当然也不会砸坏,但着实是把这个同学给吓坏了,看热闹的我们哈哈大笑,有的还说“mia呀!”每天下午有三堂课,前两节多半是常识课,包括自然、历史、地理的内容,听着很有趣味性。有时还做实验,比方把一张印有许多人像的画片装到一个带有许多窟窿眼的大转筒里,通上电一转,通过窟窿眼望去,里面的人物就活动起来了。老师说这便是“视觉误差原理”,最早的“电影”就是受到这种感悟而发明的!最后一节是自习课,老师一般不来,这是最开心的时刻,大家都非常自觉的看书学习,交流讨论,当然也少不了有个别人趁机捣乱一下,讲故事,说笑话的也不少。终于到了放学时间,大家在门外按照回家时“东西南北”的前进路线排起四路纵队。小班长一声口令:“半臂间隔向前看齐!”大家就把胳膊端起再弯曲一抄,前后紧挨着站好了队,“手放下,起步走!”于是才往大门口走,还要唱首紧跟形势的歌: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美丽的哈瓦那”、“放小驴”等等。出了学校大门口,一副热闹的场景就出现了——两边墙拐角蹲着许多精神萎靡不振的半大老头,有的摆着小人书滩,什么《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单刀会》、《武松打虎》等等,2分钱看一本,3分钱看两本;有的在卖葵花籽、糖豆豆、玉米花什么的。那时大多数同学们手里都没有钱,个别人有的话也就是几分而已,正好可以在此派作用场,掏出仅有的几分钱递给卖糖豆豆的老汉,老汉用脏兮兮的大手抓起一把把米花塞进学生娃娃的口袋之中,旁边的同学就地开始哄抢,乱成一锅粥····那个年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家普遍娃娃多,年龄都靠的很近,所以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时不时的有人来班里找自己的弟妹说事。一到放学了,各家的兄弟姐妹就在学校门口等待自家的人一起回家,我便由此记住了许多同学兄弟姐妹的名字那时好像也没有什么门户之见,男女生之间相处的很自然。当时每个同学都有一个铁皮制作的铅笔盒,盒面上印着各种精美的图画,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等人物和故事。我的前排坐着一个姓胡的女生,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她的铅笔盒上的漂亮女孩子的脸蛋上怎么都长着胡子?而且形状还不一:有的像关云长那样五绺胡、有的像张飞那样毛扎扎全脸胡、有的干脆是日本太君仁丹小胡子····我非常奇怪,一问,才知道是她的二哥给画上去的,画了又擦,擦了又画,到最后,索性不擦了。我就想,这个二哥一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因为我也酷爱给书本上人物脸上画胡子、添眼镜,就想认识一下,向他学两手,可惜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唯一能够与附小有一拼的只有实验小学,但实事求是的说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其他十几所小学就更不用提,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差的码子太大了!十五小和十六虽然各有一栋小三层楼,似乎是挺洋气的,但是校院只有巴掌大小,学生只能站在马路上做广播体操,连足球都没法踢,和我们相比,自愧不如,腰杆子首先就硬不起来。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全市小学生集中到体育馆接受检阅。自治区领导杨静仁、马玉槐等站在主席团上,各个学校的少先队员依次敲锣打鼓从台下列队通过。附小有4个大鼓、20多个小鼓,还有2把小号,十分的壮观,所以永远是领头羊。实验小学有2个大鼓、10多个小鼓,没有小号,仅次于附小。其他各个学校就没法比了,特别是十三小,仅有一个破旧的大鼓和两个小鼓。有一年检阅经过主席台时,敲大鼓的娃娃过于激动,一锤子下去,竟然把鼓皮打了个窟窿,鼓手赶紧换成左手打另外一面,谁知道热情过度,又把鼓锤子甩飞了,这可怎么办?鼓手索性用拳头敲打起来,反正领导在右边也看不见!鼓面本来就是油布蒙的,又破了一面,漏了风,再怎么打声音也是劈的,就像一个80岁的老汉在咳嗽,臊毛完了!“十三烂码头”的说法就此传开。作为附小的学生的我们既有几份幸灾乐祸,更多的还是为自己的学校骄傲!······所有的好日子都在年的夏天嘎然中止了,一夜之间,WG爆发,造反有理、是非颠倒、一切都乱了套,停课闹革命,学生变着方法批斗和殴打老师,惨不忍睹。这时的我们正好赶上毕业,四个班多名学生在操场上照了一张合影,遗憾的是,相当一批老师没有资格参加照相,因为他们已经被定性为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包括校长、教导处主任和那些老师德高望重的老师,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遗憾!之后就是长达十年的动乱,虽说我们已不是附小的学生了,但受天性所致,仍时不时地跑回去看看。上至校长,下到老师,许多人被“群专”,穿着稀里哗啦,胳膊上戴着白袖章,被“工宣队”和“造反派”整的斯文扫地、有皮没毛。就连员工老李叔也被打成“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绑着接受批斗,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骨头缝里拔凉拔凉的·····尘埃落定之后,附小先是改名为“七·一学校”,后来又改成“银川市21小学”,再往后,又在本部之外陆续办起了“分校”,摊子越铺越大,战线也越拉越长,当然名气同样也越来越响。我家的儿孙之辈也都先后在此读书。可以说,这个学校成就了我家几代人,因此我本人始终对它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当我又站在这所学校的“分校”门前时,满脑子都派生出对儿童时代的回忆并不为奇,作为一个甲子前的老校友,我也衷心祝愿21小的明天更加美好!我的儿子 、10、9、银川郝寒冰散文我的朋友苏峰郝寒冰散文|左旗的同学郝寒梅散文 8月·秋日的银川郝寒冰散文 年的红舰郝寒冰散文|有关“宁大话”的故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xj/9331.html
- 上一篇文章: 嘉德秋拍ldquo中国人民的老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