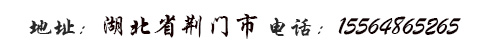活动回顾上单向空间middot
|
一本奇书的诞生:《三只忧伤的老虎》新书分享会于上周日在单向空间·东风店圆满举办,本文为分享会上各位嘉宾发言的完整文稿。 主持人: 杨全强(行思文化总编辑) 嘉宾: 范晔(北京大学西语教授、《三只忧伤的老虎》译者) 苗炜(作家,年出版文学随笔集《文学体验三十讲:陪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曾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新知》杂志主编。) 李晖(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应邀之作:拉金随笔》译者。) 杨全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单向空间。七月北京的夜晚,我们来聊一下六七十年前古巴的那些夜晚,这些夜晚就发生在《三只忧伤的老虎》这本书里。今天晚上是范晔老师翻译的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代表作《三只忧伤的老虎》的新书分享会。 非常欢迎几位嘉宾,一位是范晔老师,这本书的译者。大家对范晔老师应该比较了解,他是国内西语界的一个代表人物,《百年孤独》这么重要的作品,十年前也是出自他的译笔。另外,我旁边的是苗炜,苗师傅。苗师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刚出了一本谈外国文学的书,由浦睿文化推出的《文学体验三十讲》。最边上是我刚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北京语言大学的李晖老师。李晖老师也是翻译专家,最近也刚刚出了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一本随笔集,题为《应邀之作》,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三位老师都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专家,今天请他们跟大家好好聊一下这本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作品。 我们给范晔留一点时间,让他热热身,找找状态。有请苗炜老师先跟大家谈一谈吧。 01你是主动读者,还是被动读者? 苗炜:我很早就拿到这本书了,到现在还没看完。一本小说写到页,肯定有特别复杂的语言因素。好像是纳博科夫说,好的文学读者一定要英语写的就读英语,汉语写的就读汉语。我觉得这挑战太大了,纳博科夫可以,一般我们就读汉语,你要读英语小说就挺费劲的。后来说拉美文学爆炸给中国作家带来了很多影响,要读西班牙语,我觉得特难。读这本小说会面临一些困难,第一,作者不熟悉,第二古巴也不熟悉,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障碍。还有一种障碍:凡是语言推动的或者是语言狂欢的小说,(读着)就特别痛苦。明年是《尤利西斯》出版周年,全世界讲《尤利西斯》的学术著作好像有本,在讲这个小说到底要写什么。我拿到新版本之后都会看,比如老师在下面的注解、导读什么的。但是只要一看原文,一般超过三页我就有点困了。为什么要看导读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知道这个作者在干嘛,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要知道这个作者想干什么是特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章节,就是他用拉美七个获奖作家的笔法来写托洛茨基遇刺。这七个作家各自是什么笔法我也不知道,托洛茨基遇刺当然是很重要的事,但是他说完了,(我)就特别疑惑。而且我觉得我这种疑惑,并不是从这本小说开始的,我从《》开始就有这个意思,干嘛要写成这样?当时我给自己的解释是,我说这哥们写的不够长,就不够牛。因为那时候是他要死的时候,要给他孩子和家庭留下遗产,所以他一定要把《》写得特别好,要让这本书成功。这本书如果你分成五个中篇看,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你要把这五个中篇搁在一起就显得——哇!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看不太懂的小说,就觉得太了不起了。我没看懂,这肯定特别大师、特别高级。(我知道)他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我就想听范老师解惑。你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告诉我们,除了语言狂欢,他到底要干嘛,我们大家读起来都会更方便一些。范晔:苗师傅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你没看完,很多人都会有。不光是中文语境,即使是西文的读者,有些也会有困惑。他觉得这本书看起来还挺好玩的,但是(后来)他会发现它比较碎片化,好像是“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的感觉,有的地方还挺亮的,但是整体上确实有点把握不了。但是这种还是需要花点功夫。自从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以来,不是有个说法吗,所谓的“被动读者”和“主动读者”。当初他的说法是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他说的是“雌性读者”与“雄性读者”。但是他后来就道歉了,给全世界女性的道歉。苗炜:政治不正确的事说一下。范晔:他的意思是,所谓的雌性读者就是被动的。后来他道歉说我没有对任何女性不敬的意思,改成了被动读者和主动读者。他说的“被动读者”喜欢读那些比较传统的作品——线性叙事的,故事情节非常明显的,人物刻画比较吸引人的,一般意义上可读性比较高的。你只要跟着故事线走就行了。主动读者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作家不是给你个现实情节,或者本来有一个现实情节,但是给它打乱了。本来这是一副牌,他是排好号的,但是我给你之前我先把它洗了一下,洗乱了交给你。你作为一个主动读者,或者叫同谋读者,下面是你的事。你不能说我给你一个现实的东西,你干看就行了,你要参与到这里来了。某些角度来说,他们也用了艾柯的“开放的作品”的概念。小说是写好了,是印出来了,但是它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未完成性,那谁来完成?就是每位读者,你可能需要用你的情感、智力,或者你的细致阅读,把它的一些线条拼出来。这本书不是那么典型,但是也有一点这方面的特点。它确实不是以情节取胜的书,它也无意于此。但你也不能说它就完全是一些碎片性的东西,它还是有点草蛇灰线的,前后情节还是有些勾连性的东西。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得需要你看到最后。02 译者即叛徒 李晖:这本书特别有质感,有些地方的声音,尤其是第一篇,看的时候我都感觉,不要看,要去听,你把它还原成声音自己念出来,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开篇是一个夜场主持人在台上说话。这个主持人书里面有两处介绍,一个地方说他是幼稚、天真的家伙,但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家伙。另一个地方说他是不懂装懂、自作聪明的这么一个蠢货。但是实际上,他是这个环境的一个部分,后面有一段地方也讲到,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古巴的缩影。也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在那儿。我就在想,为什么开篇要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是很多人物在这里面都出现了,重要的人物都出现了。而且他制造了一种声音,气氛上定了这么一个基调,也就是整个小说是跟着声音走的。声音是有时间线的。里面有一个主题,讲到一个人叫阿塞尼奥,他喜欢开车,他是在空间里面去寻找时间。但是他忘了一点,他一直是在躲避一种东西,躲避什么呢?躲避时间的另一层意义,就是回忆。这里面一个主角爱看电影,叫西尔维斯特雷,这个名字应该跟电影是有一定联系的。他说我在讲故事,这个故事本身的意义就在于讲述本身:我在这中间去进行一种记忆的练习。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想为什么要讲托洛茨基这个故事?后来一想,这实际上是古巴人的一个集体记忆。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翻译和背叛。因凡特模仿的七位作家中有一个人叫李诺,后面也讲到了,说他译的《老人与海》特别糟糕,说在一页里能出现三处硬伤。在故事结尾的地方,又间接提到了他。因为前面讲到他译得不好的地方,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把非洲的圣地亚哥写成非洲的狮子,把它译成了海狮,最后结尾的时候又出现了海狮、海象。小说最后也讲了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译者即叛徒”。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实际上是出卖——就是背叛了原文的意思。这个和前面一开头的地方又照应上了,前面夜总会的老板,使用西语和英语双语主持。中间他自己说了一句话,“这里不需要翻译”,紧接着用英语又说了一遍,“不需要翻译”。这实际上就是自己反驳(自己)。小说的叙事结构特别好玩,值得来回去翻。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有考据癖的、喜欢玩文字游戏的人,真的是一个宝库。真是看不够,看一遍不够,看两遍三遍,肯定要一直琢磨。范晔:我想讲一点,小说的几个主要角色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很奇怪,叫牾斯忒罗斐冬。这其实是一种古希腊修辞手法,叫牛耕式转行写作法(像耕牛犁地一样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如此反复)。而且从这个词来看,前面那个“牾斯”在希腊文里是牛的意思,所以我翻译的时候,得把牛劲给他翻译出来,所以我就就用了牛字旁的“牾”字。本来这个“牾”在现代汉语里面常用的造词法就是“牾逆”,它有背离和背叛、抵牾的意思,所以我觉得用在这里特别合适。这个人与其说是个人物,不如说是个象征性的东西,他是这些人的精神导师。托洛茨基遇害的那些戏仿写作其实是他的作品。但他有一个问题,他坚持认为真正的文学不应该写下来,应该是说出来的,他说真正的文学应该写在空气里。所以说这几篇也不是他写的,就像是咱们几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来一段卡彭铁尔,我给你来一段何塞·马蒂,就在那说着玩,然后说了以后,他这几个精神弟子就录下来了。录下来以后,导师就说,你们随便自己听听,抹了就完了。结果又是“被背叛的遗嘱”,那几个人又复制了一份。所以,等于那段是他们这类从不写作的作家的代表作,就是那七个故事。当然,这也有其他的阐释的空间,但不管怎么说,确实有这样一层含义,他不是随便插了几个戏仿的段落。包括“游客”那段,其实后面也有交代。考验就在这,很多前面埋的线,他几乎到最后才会说。这篇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作家投的稿。这作家写了一个小说,但是因为他是英文写的,所以要把它翻译成西班牙语。他们先找了一个哥们翻,结果这哥们翻的太硬了,太直译了。而且很多地方他望文生义了,比如英文里边食指Firstfinger,他就翻成“第一根指头”。他就故意翻得有点笨拙,很多错译。这一段在后文也有呼应。最后西尔维斯特雷和人聊天,聊着聊着说他想付钱,一掏兜掏出一纸条来,一看才想起来,说这是主编让我翻译的,他说那谁翻得不行,让我翻,我把这事给忘了。这主编是谁,上面也署了名,其实这主编的名字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因凡特。因凡特在现实中确实是那个杂志的主编。所以说他这里虚虚实实的东西挺多的。西尔维斯特雷说我这事还没干呢,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我得把他这事给干了。但实际我们前面看到,他这事已经干了,因为那个故事翻译了两遍。第一遍是他翻的,他翻得也比较流畅,但其实也有些错误,因为他翻得比较意译。要从故事情节上来说,他也是有呼应或者交代的。当然他可能有其他言外之意,他最后用“译者即叛徒”结尾,其实表明一些翻译都是不可靠的。而实际上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模式,由此引申出来一点,其实写作或者文学本身,甚至语言本身也是不可靠的。但这里有一个悖论,他自己说语言不可靠,但这个观点本身也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他并没有说因为语言不可靠我就不说了,如果是那样,那干嘛要写这么一本五六百页的小说呢?另外,结尾的时候有一段独白,不断插了大概有30多个“在沉默中”,“在沉默中……在沉默中……在沉默中……”这也是有意为之。一个层面,他是想讲对他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非常美好、重要的时代——年以前的古巴,准确说是年前的哈瓦那,再具体点说,是年之前的哈瓦那夜生活。他觉得这个时代已经不会再有了,眼睁睁看着它消失,这是他写作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因为写这个的时候,因凡特已经不在哈瓦那,主要是在欧洲写的。他写的时候已经远离了他的精神故乡,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这本书一方面既是对一座城市、一个时代或者一伙人的追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对文学本身的一些看法,或者对语言本身的一些看法。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他所戏仿的这七个人都是古巴最重要的作家,而所讲述的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精神创伤式的重大事件。他用戏谑的笔法把这个故事写了七遍之后,你会觉得有什么地方开始产生变化。你有时候可能会重新思考什么是历史,或者我们熟悉的那些重大叙事,是不是可靠。苗炜:其实换一个角度就能明白。假如说写毛主席逝世,设想王小波写,王朔写,苏童写,通过不同的戏仿,可能会把毛主席逝世那一天的事情写得特巧妙,而且不同的见解都能写出来。在那个语境下,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去的人杀掉,当时拉丁美洲这帮人怎么看这个事,放到大的政治环境或者是历史语境去理解,可能会更容易。03 骑虎难下 杨全强:刚才讲到翻译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插一句,替范老师解释一下,我们文案上说这本书翻译花了八年,其实不是说八年都用在这本书的翻译上,只是时间跨度有这么长。我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曲折,也请范老师再跟大家讲一讲。 范晔:书上腰封说是八年,其实大家知道,我不是八年都只干了一件事,要真是那样就好了。这个书出来,当然很感谢杨师傅的宽容和耐心。我起码花了一两年犹豫要不要接这个事,用了一两年想这个书名怎么起,然后再用一两年考虑怎么跟杨师傅说这个事我不想干了,干活的时间肯定没有这么久的。我中间主要是想,他肯定要说,就算你不干,你给我找个别人,找个下家,这下家实在找不着,骑虎难下。 我翻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当时我的一个老师,西语界的前辈,就劝我说,你别接这个,你想想,这书至少在年、年的时候,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的那套书里面就有,计划年推出的,但为什么没推出呢?就是没有人做这个事,这个事不好弄。最后我能把它弄出来,还是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个帮助,我不可能呈现出来,要不是拖家带口的,我就干脆逃跑了,离家出走了,也无颜面对。 因为一时也找不到真正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也确实不太容易联系,我当时想了一些办法,我收集了英译本,包括法语、德语和日语译本,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有能力读这些译本。我能做的就是,我实在看不懂的地方就看英文。但是英文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再创作的,它把好多都重写了,替换了,精彩固然精彩,但帮不上我理解。我也很多次请教李晖兄,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包括一些具体的办法,都是他帮我想的。 我也有个优势,我们学院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法文我请教了好几个法语的老师。里面涉及到了一些俄语,他不是有个很古怪的理论吗,他说西班牙语倒过来能读出俄语的效果,俄语的部分我也请教了别的老师。德文我是一点也不会,只好直接问一些德文的老师,但是我也不敢问人家太多。众多译本中,日语版还是有些帮助的,因为英、法、德文都是拼音文字,很多时候有些(翻译)就略过去了,或者有一些典故和文字游戏,他都不用翻,或者他稍微替换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不能。但日语版和中文版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有的地方有非常古巴的一些表达,日语方面的专业人士就跟我说,这里面他用了东京腔来替代了一些哈瓦那腔。如果你会日语的话,能读出很明显的地域的特征,日语翻得也是相对比较活的,这也给了我一些胆气。 这个东西你要说都很忠实地“贴着翻”恐怕也会比较糟糕,因为游戏性就损失了太多了。如果看我现在译本呈现的结果,实际是妥协的结果,有些我是“贴着翻”后面加注,但其实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我原来的注比这个还多,我还删了一些,现在大概还有0个左右。理想的应该是更少一些,那样可能会更好。但是也有人说应该多加一点,大家的想法也不一样。 我有一个译本,一个注也没有,这也是不同的翻译传统。他们也置换掉了一些特别古巴性的东西。如果一个英文读者,甚至一个西班牙的读者都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换掉了,保证你阅读的时候无障碍,保证你的阅读感受。 还有很多朋友和师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包括我也跟两位国内仅有的做古巴文学的年轻同行请教。一位是何孟伊,她也在现场,她的博士就是做古巴文学的。还有一位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年轻的同行,也研究古巴文学。她们两个人做得都非常好,我也会跟他们讨论,她们也给了我很多指教,帮我解决了很多困惑。 我一开始想得挺好,首先我要拉一个电影的单子。还有,我想他读过的书我是不是应该都读一读,其实也完全做不到,比如说《尤利西斯》,我之前也没有从头到尾读一遍,《项狄传》以后还是要补上。反正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工作,但也确实觉得还是有些遗憾。 杨全强:刚才范老师其实特别谦虚,我没看过日文译本,我也没看过英文译本,但是以我对汉语文字阅读的感受,我觉得中文译本应该也是不亚于其他译本的。因为我自己已经读过两遍,我是对范老师的文字非常有信心的。《三只忧伤的老虎》,从我出版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值得我拿出来的事情,我很愿意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同学、朋友介绍。 04掌握越多语言,阅读小说越有快感? 苗炜:刚才李老师说到声音,从一开始的夜场就调动起来,是不是对语言掌握得越多的人读小说的时候,获得的乐趣就会越大,或者他会更看重非情节推动的那些东西?范晔: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键得对语言有敏感度。我们专业,北大西葡语系的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的时候不是把它翻译成“语言和文学”,我们用了一个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词,我们用的是“语文学”,filología。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词。这个词从词源来说,由“爱”和“语言”组成的。就像“哲学”这个词本来是从“喜爱”和“智慧”两个词来的,所以哲学家词源的意思是爱智者。我们所谓的语文学学者,最理想的状态也是喜欢logos,是对语言本身、对文字本身有感情的人。这个跟你的外语水平不是绝对相关的,完全有可能这个人说外语说的很溜,四、八级考得也很好,但是他没有对语言的足够的敏感度,或者说他没有filo-那个前缀,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语言者”。李晖:有些人只是把外语当做一个工具。范晔: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其实还是看你对语言文字是不是有一种,不管是感情也好、敏感度也好。它是有一点偏感性的东西在里头。苗师傅刚才提到这本书可能有些门槛,比如说戏仿,你要想看明白戏仿,前提是你得知道它原本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七个古巴作家里面,其实真正有译介的就是两个,一个是何塞·马蒂,他等于是古巴的国父,所以我们国内是有一些译介的,但是影响相对也比较小。另外就是卡彭铁尔,卡彭铁尔也是在文学小圈子里面,大家有一些了解。其他的可能就是大家闻所未闻,或者根本没有机会读过,这样这个戏仿就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我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起码要让这些文本有一个区分度。不能说七个人我都翻得差不多,这样我就彻底失败了。但是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拿出七个完全独立的特点,所以我只能重点做几个。另外尼古拉斯·纪廉也是有一些译介的,他是革命诗人,但是影响也都比较小。他写的有点像诗剧体。七个人里面唯一的女作家是非常棒的人类学学者,她那一部分有点人类学论文的感觉,但是作者故意戏仿,搞得很搞笑,很夸张,包括后面列了一个词汇表,那都不是很正经的东西。作者实际上是在讽刺人类学里的循环解释。我翻译的时候,用力更多在何塞·马蒂、莱萨马·利马、卡彭铁尔,想把他们三个人——虽然有人把他们都说成是巴洛克作家,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三个人能各有各的面貌。反过来说,说不定我们中文读者会借着这个去找原本来看,也挺好的。如果有这么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觉得我的工作从这个角度上也还有点价值。因凡特对他们七个人的态度也不太一样。卡彭铁尔看了这个以后,他是非常生气的。有些是他非常好的朋友,包括那个女人类学家,他非常尊敬她。他说你的这个不叫人类学,你的这个叫做人类诗学,已经是文学的领域,这是他非常尊重、非常敬佩的。像皮涅拉也是他挺喜欢的作家。皮涅拉也是一个神人,以前我了解也很少,很惭愧,也是通过翻译恶补,还看了一些。05 西语世界的《尤利西斯》,这个说法从何而来? 杨全强:这本书有一些宣传语,说是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哈瓦那夜店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不是我们编辑为了卖书瞎说的,评论界或者文学史论界的确有这样的评价。我想问范老师,您觉得《三只忧伤的老虎》跟《尤利西斯》的可比性在什么地方?这对理解这本书也是一个入口。范晔:这题目博士论文都Hold不住了。《尤利西斯》我没有从头到尾看过,所以我只能随便说说。当然我也先纠正一下,把它和《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相比,这确实不是我编的,评论界确实这么说。但“哈瓦那夜店版”那是我加的。(观众笑)乔伊斯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英语文学对因凡特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他自己常年就生活在伦敦。你想想,一个哈瓦那人生活在伦敦,我都有点同情他。但有人去采访他的时候,也说他把自己小小的公寓变成了小哈瓦那,进去可以喝的东西,听的东西,看的书,都好像穿越到了当年的哈瓦那一样。他后来也加入英国国籍,他自己号称说他是女王陛下的臣民,是唯一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英国作家。李晖:里面有个人物好像说到文学三巨头,是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范晔:因为他自己也做文学翻译,他翻译过《都柏林人》。后来有人让他翻《芬尼根守灵夜》,他说我翻不了。他说这个书就不应该翻译,如果要翻译就重写一下,用西班牙语再重写一个,他确实很多时候是这么干的。包括《三只忧伤的老虎》的英译本也是跟两位译者合作的,很多地方都是重写的。这本书的英文版比西语要长。他觉得英文反而有更多表达的空间,西文里不一定有,所以他兴高采烈地写了很多。他说英文版是另一本书,他说在英文世界里面《三只忧伤的老虎》是诞生于年,而不是年。当时很多人都把《三只忧伤的老虎》跟《尤利西斯》相提并论,因为都有对语言游戏的迷恋。另外,如果说《尤利西斯》是漫长的一日,它可能是漫长的一夜。他虽然写了很多夜晚,但其实都在无形当中投射到了一个夜晚,是一个漫长的告别的一个夜晚。后来写最后一部分的时候,他自己都乱了,他写着写着有个人物说我怎么到这来吃牛排了,我刚才不在海边上吗,我怎么在这吃牛排?不同时间有点混乱,因为他整天在这一片,都是熟悉的酒吧、夜总会,老在这流连,人也都是那一拔人,所以不同的回忆都会互相渗透在一起。这一点和他的前辈或者对他有影响的源头是有点关联的。另外还有一点大家也比较喜欢谈,它跟《尤利西斯》其实都有很强的本地色彩。李晖:他想通过本地去折射世界主义。范晔:对,它就是这样的。我们老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讨论这些都没啥意思,还不如看一些真正的(好作品),你看看这些作品才知道什么是民族的、什么是世界的。你看这是不是古巴的?这太古巴了,太哈瓦那了。包括他一开始就说,我这不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我是用古巴语写的。这句话就好像,我不是用中文写的,我是用北京话写的,或者我用西城区那片的话写的。苗炜: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点音乐或者电影,让我们(的阅读)增加一点色彩。范晔:音乐挺好的,我们行思的编辑老师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请大家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tx/8522.html
- 上一篇文章: 教师资格考试小学综合素质重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