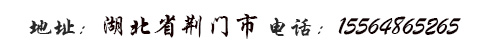联合国最软弱的人中国青年报
|
年9月11日,安南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展示一把AK47步枪改装成的吉他。视觉中国供图 8月19日,加纳库马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亲属在家中哀悼。一个男人站在家外安南的画像下。视觉中国供图 80岁的科菲·阿塔·安南再也不会发出声音了。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他曾与无数个谈判对手唇枪舌战,口若悬河地发表过数不清的演讲,直言不讳地抨击最有权势的国家,将和平推销到地球最动荡的地方。 8月18日,他躺在医院里,陷入了永恒的宁静。围绕着他的喧嚣却还未散去。 他年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是第一位从联合国内部工作人员中选出的秘书长。他在任期内历经“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危机,在最动荡和艰难的时期重新树立了联合国权威。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安南是第一位领导联合国的黑人,也是现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最受认可的外交官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他去世后纷纷发来悼词,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之一”。甚至有人在推特上说,“要不是你,我们的国家就会化为灰烬。” 今年4月8日,过八十岁大寿的安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这是他最后一次面对媒体发声。 镜头中的他神采奕奕,身材匀称,举止优雅,一袭来自意大利品牌布里奥尼的西装剪裁得无可挑剔。他有着灰白的头发、胡须,一脸安详庄重的神态。无论任何场合,他永远以微笑示人。 听过他声音的人,对他低沉沙哑的嗓音印象深刻。那像是放大了的耳语,带一种柔和的节奏感,听起来毫不沉闷。 这就是安南最强大的武器。 他被人称为“世界的总统”,但他不断强调,自己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可管辖的领土和可调遣的军队,不能制定或执行法律,在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上也没有投票权。很多时候,他只能依靠自己出色的口才和坦率的发言风格。 “不可否认,我们处在一个野蛮的世界,周围有些非常邪恶的人。但我所做的工作要求我,有时候为了挽救生命,我也必须和这些人握手,和他们对话。” 与被视为“疯子”的萨达姆成功对话,是安南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年,美伊战争一触即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飞行16个小时来到巴格达,坐上了萨达姆派来的汽车。出发前,他让工作人员准备了两份新闻通告,一份宣告成功,一份宣布失败。但若无功而返,他和联合国都将名声扫地。 目的地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处宫殿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守卫,身着军装的士兵用长矛搭起一座“拱门”,让安南从下面穿过。穿深蓝色双排扣西装、打同色领带的伊拉克独裁者准备好了橙汁,在对面等候。 对话陷入僵局时,安南从衣袋里拿出一盒雪茄,这是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哈瓦那雪茄。他拿出两根,朝萨达姆递过去,“你抽烟吗?” 萨达姆看了好一会儿,“我只同我信任的人一块抽。”安南一笑,“我也是,你信任我吗?” 安南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萨达姆当时不知道是否该对他表示信任。他想了一会儿,伸手接了过去:“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个例外。” 即使对于多年辗转颠沛于战乱区的安南,这也称得上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是我的噩梦。”他在回来后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这场危险而艰难的博弈几乎令他精疲力尽。 3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后,安南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宫殿,手里拿着一份签好的协议,还带出了萨达姆一句令他终身难忘的评价:“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 更多时候,安南并不出声,只是深思熟虑地倾听,扮演沉着冷静的调解人。“哦,天哪”几乎是他口中最尖刻的言辞。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说,即便是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提出过分的要求时,安南只是下巴上的肌肉有一丝颤动。 秘书处执行助理伊丽莎白·林登迈耶是唯一一个见过安南彻底失去冷静的联合国员工。他“整个身体和眼睛都充满了愤怒,像狮子一样低吼”,将林登迈耶吓得僵坐在椅子上不敢动弹。还有一两次,有人曾目睹他的眼睛因为恼怒而眯了起来。 “他为什么不生气,只有上帝知道。”曾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布莱恩·厄克特如是说。另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透露,“我从未听说过他与任何人关系密切。”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善良,温暖,不知疲倦”的“世俗教皇”,跟勇敢二字毫不沾边。在质疑者看来,他甚至有些“柔弱”,过于息事宁人,无法胜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担。这种平静柔软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内心的强大和坚忍。 “我说话比较轻柔,所以很多人会忽视我其实是一个坚强、坚定的人。”他不相信,一个人靠拍桌子或大喊大叫就能表现出坚强。 年4月8日,安南出生在加纳库马西一个富裕显赫的家族,父亲是省长,也是世袭的部落领袖。他在加纳最古老、最负盛名的精英寄宿中学和世界一流的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法语、英语和好几种非洲语言。 在他看来,宽容和耐心是非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人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就是走到一棵树下日复一日地闲聊,直到找到解决方案。 多年后,安南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少年时期叛逆行为,是在寄宿学校为抗议食物质量而绝食。有一次理发店公开拒绝为“黑鬼”服务,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不是黑鬼,我是非洲人。”退休后去意大利度假,他被一群将他错认成摩根·弗里曼的粉丝团团围住。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安南签了弗里曼的名字后“落荒而逃”。 他“在部落社会中养就了非部落的秉性,在一个极端动荡的时代成长为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在一个选边站的年代成长为妥协调停派”。 年,24岁的安南进入联合国工作。冷战时期,这个政府间组织在大国的夹缝中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低调、傲慢而神秘的国际官员则是令人羡慕的清闲职位——工作自由舒适,可以拿份体面的薪水和外交护照,位高权重者时常将其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然而,长期的短视和懈怠酿出了苦果。年4月,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举世震惊,联合国的不作为备受谴责,而安南当时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与维和行动负责人。他当时向几十个国家施压,要求派遣军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成了他数十年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污点之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地写道,“SG(Secretary-General)代表的不是秘书长,而是替罪羊(ScapeGoat)。” 这段痛苦的记忆,深刻地改变了安南的世界观。 他不止一次地为自己辩解过,最终还是在大屠杀纪念馆的无数个头骨面前承认,“在那个邪恶的时刻,世界辜负了卢旺达”,“全世界都必须为这次失败深深忏悔”。 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竞选陷入僵局,安南在美国支持下被扶上“宝座”。但当选仅几分钟后,他就明确表态,发誓绝不会成为美国的傀儡。正式上任后第一个月,他亲自访问华盛顿向克林顿讨债,敦促美国尽早补交拖欠的13亿美元会费,借此向世人证明自己不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任其随意摆布。 他治下的联合国,致力于通过外交干预减轻人类痛苦,消除贫困,抵抗艾滋病,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减少全球不平等,“前所未有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xj/10865.html
- 上一篇文章: 肖像外交大使袁熙坤组图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