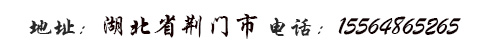行走的瓜蛋儿三
|
治疗白癜风的专科医院 http://www.bdfyy999.com/index.html行走的瓜蛋儿(三) 作者▏尘埃 加勒比海上的蓝色鳄鱼-古巴(下) 哈瓦那街景年12月,时隔七年,我又踏上了哈瓦那这片热土。 这座城市的风貌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仍然是曾经的繁荣交织着经年的破败,沧桑伫立,不同的是空气里飘来了欢歌...... 年4月1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正式当选为古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古共“六大”确立了经济和社会模式更新,明确了改革方向。坚持不快走也不停顿的原则,扩大私营经济、建设经济特区、废除货币双轨制、国企改革、吸引外资、减少国家干预、简政放权、改善民生......2015年7月,与美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对于旅游者我来说,发现的变化是民宿迅速增多,旅游业开始出现了竞争。F先生家的民宿在第一波竞争搏杀中倒下,不再经营民宿。 我多次到老城的R街去找昆多,都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在街上看见巡警,我都要打量一番,辨识他们是不是昆多?但他们都不是。 昆多是换岗去了别的地方,还是下岗了?我的新朋友,绰号叫“火种源”,是中国公派到古巴的留学生,来哈瓦那学医已两年多了。他给我预定了一家民宿。 民宿主人是H先生。H先生是医生,会西班牙语、英语,还懂一点法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游客中有很好的口碑。当然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在互联网普及率仍然很低的哈瓦那,医生家能保证有互联网,这使得游客蜂拥而至。 H先生家只有三间客房,住不下的游客,他会把他们介绍给其它民宿。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放开了本国汇款到古巴的额度限制。听说古巴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都是靠美国亲戚的经济援助致富的。H先生家也在其中,他家的房子是上百年的殖民大宅,外观陈旧,室内装饰布局讲究,大客厅里摆放着仿古家具,还有一台老旧的钢琴。 总有一些不是H先生家的住客,会到这间客厅来蹭网聊天。H先生不计较,对这些人敞开大门,久而久之,H先生的客厅就成为当地有知名度的游客沙龙。在游客沙龙里,我看见了A太太,加拿大人。她到哈瓦那来的唯一目的是学习正宗的古巴萨尔萨舞(又叫莎莎舞)。 她说萨尔萨舞是一种强调个性化、自由不拘、雅俗共赏、激情四射的热舞。她年轻时就很喜欢,现在退休了,有时间来学习,想成为一名资格的萨尔萨舞舞者。 我问她有孙娃吗? 她说有五个。 我又问她:你的孙娃们需要你带(照顾)吗? 她说:为什么需要我带?我把儿女们抚养成人了,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该我的儿女们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差异,这就是不同人群的观念差异,在中国,好些与A太太同龄的人,忙乎着带孙娃......在游客沙龙里,我还遇到了B先生,英国人,三十多岁,在联合国工作。他利用休假到古巴,见识即将远去的社会主义。接着他还要去东非的乌干达,我估计这行的路费不菲。 在中国,我们也许会把这些钱存着,做房子的首付或按揭。 我问他英国的房价很高吧?按揭压力大吗? 他说:伦敦房价很高,按揭也有压力。可是,我不认为一定要买房啊,租房在我们国家的中、青年人里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到了有能力、有必要买房时,有些按揭也会一直持续到退休。说这番话时,他显得很淡定,没有一副压力山大的样子,即使不买房也不影响他去看大千世界。 嗯,这也是差异,在我们那里,没有房子找老婆都难。在游客沙龙里,还有C、D女士及先生的见闻,就不赘述了。劳动人民 火种源来找我了,他要带我出去逛逛。 我对火种源留学的情况有兴趣,一路上都在问他。他说:他所在学校的前生是一家叫达拉拉的疗养院。 年4月26日,乌克兰(前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当时释放出的辐射线计量是二战时期投到广岛原子弹的倍以上(此数据来自百度百科)。在这次事故中死亡及受到伤害的人数至今有着不同的统计数据。 达拉拉疗养院,在那个期间,接受了一万名左右来自乌克兰的核辐射受害者,让他们在该院治疗。他们大都是年轻人,也大都先后在还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少数活下来的人,有着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是人类一次深刻的教训,给世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疗养院的使命完成后,政府就把它改成了医学院,有中国留学生在此就读。 他还说:古巴的医学和医疗体系超越了其它发展中的国家,甚至有些医学科目不逊色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外交也是这个国家的利器。我们国家近年来与古巴的关系有缓和,对他们有支持和援助。他们的回馈之一就是每年给些名额,免费给中国培训一些医务人员。中午了,火种源推荐了一家价格亲民的餐馆,我们入座就餐。喝着啤酒,吃着拉丁风味的菜,我看着窗外的行人......有当地人在使用手机、在喝矿泉水、在喝可乐! 此刻我又想到了昆多,此时,他也许在烈日炎炎的某个街上巡视,也许也正拿着一瓶可乐在喝,而不是转身急于找小商贩把它卖掉......一种酸楚交织着欣喜涌上心来,我拿着啤酒杯对着窗外,为昆多举杯......火种源继续说他的留学经历。 他说:我所在的那所学校条件较差,生活条件远没有中国好,我们多次投诉也无效。一些同学不安心学习,有机会就去做挣钱的事。 我有个同学绰号叫“擎天柱”,前几年清凉油紧缺时,他捣鼓这个生意,不仅赚了一些钱,还认识了红白道上的人,把路子打开了。现在他伙到北韩住古巴的某官员,从中国进货,进入了哈瓦那小商品市场。我在给他当马仔,累是累,有搞头。 我问他:那你给擎天柱当马仔,还顾得上功课吗?会影响你的毕业吗? 他毫不犹豫地说:毕不到业就留下。古巴的发展空间很大,像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有发达致富的机会。我与他干杯,祝贺未来的“火总”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火总”一高兴就夸下海口:到时真当“总”了,就请你到哈瓦那最高档的餐馆去嗨一顿,哈哈哈...... 这家餐馆的炸肉饼很好吃,餐后,我又要了两份,与火种源各自打包一份,带回去当晚餐。街头巷尾 喝了啤酒,我头晕乎乎地,走出餐馆,我与火种源分手,准备回民宿去休息。 推开民宿的门,看见儒雅的H先生正拍着桌子和太太在吵架,太太也不示弱,拿着一个玻璃杯,比划着要摔的动作(就是高高举起,就是坚决不出手的架势)。 见到我,两人开始克制,但H太太的怒气惯性还不能立刻刹车。她沙哑着嗓子说:哪种社会制度好,用事实说话。你当初给我的婚戒就是一个塑料仿石头的,说经济状况好了,给我买个资格钻戒补起。你又当医生我们又开民宿,三十好多年过去了,那个资格的东西在哪里?那个老家伙的兄弟接班当上了领导,一边说改革,一边又说革命尚未衰老,它依然很年轻,听到革命两字,我就崩溃...... H先生赶紧压低着声气说:小声点!小声点!!你懂个屁!!!一枚钻戒就能说明一个制度的好坏吗?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制度都有好坏。我们的儿子总不会倒在校园的枪击案中,我们也没有大楼去拿给飞机去撞击,我们都是低矮的房子......关于这类牵扯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我是无法断公道的,而且也劝不来架。我把拎在手上的炸肉饼递给H太太,H太太打开盒子,惊喜地叫到:啊,啊,这么好的肉,是给我们的吗? 我对她点头,她手舞足蹈地对H先生说:快去打电话,叫何塞他们(儿女们)都回来吃晚饭,你也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我说不用了,休息一下,我要去看大公墓。哥伦布纪念公墓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条件允许的话,我会去公墓转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个人嗜好而已。H太太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她说她的母亲就安葬在那座公墓里,也该给她送一支花去了。 在去公墓的途中,H太太给我讲述了她的一些家事。她的娘家是西班牙后裔,在年那场革命前,她的父亲是一个农场主。革命后,政府进行了土改,把全国大约25亿美元价值的人民私有财产国有化了。H太太父亲的农场也在劫难逃,革命嘛总是要流血的,她的父亲也在那场血洗中去了天堂......她还说每次和H先生吵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家务事和孩子们的事,也不是为了那个塑料戒子,而是我们对国家制度的看法势不两立。 可以理解一个失去家族农场、又失去父亲的女儿,一生有无法剥离、附着在血液里的痛。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痛,使她对“革命”有着不能释怀的成见。墓地掩埋着许多光阴的故事。我给H太太说,你给你母亲献花后,不用等我,我要独自呆一会。这座公墓叫哥伦布纪念公墓。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墓,占地近60公顷,埋葬了约二百万人,建于-年间。碑文几乎都是西班牙文,我看不懂,只能一睹墓地的宏大壮观,再细观一些碑文上逝者在世的时间。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是上世纪的移民,当年为求得更好的生存,漂洋过海,将自己生命在中、青年时,就定格在了加勒比海岛的蔚蓝里......公墓雕塑值得一提的是,在墓园一侧的墙外,一路之隔,有座华人墓地—中华总义山。一眼望去,颓垣败壁、荒烟蔓草、西风残照下,一派凄凉......原来这里长眠着一些华人,其中有十九世纪末,被西班牙商人骗到古巴来淘金的华工。 这些华工抵达古巴后,都在农场(甘蔗种植园)做苦工,相当于奴隶,生活非常悲惨,其中一些华工不堪忍受苦难而自杀。这也促使部分华工后来奋勇参加了反抗西班牙殖民地统治的武装斗争,赢得了当时古巴领导人“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和叛徒”的赞誉。 由于这些华人不是天主教教徒,不能安葬在哥伦布纪念公墓里,于是就这样了,挨在大公墓的一边,低吟着殇歌......看来土葬未必是最好的归宿,其实海葬也不错,做大海的儿女,至少不会有这般颓败像......我没有带酒,只好泼洒矿泉水,祭祀这些天涯海客。接下来的两天,我去了巴拉德罗,一个最不像古巴的海滨度假胜地。20公里的白沙滩、清澈的海水、斑斓的海底世界、湛蓝的天空、绮丽风光、治病的泥潭......这是上帝赐予这方土地的伊甸园,度假的人几乎都是外国人。写景不是我擅长的,就此省略抒写。回到哈瓦那,在我要离开的前一天,我又遭贼了。 这次我的手机一直捏在手上,始终是安全的。但是我背包的拉链被人弄开了,把我余下的红比索偷光了(货币仍然是双轨制)。我去银行取钱兑换,被告知我的银行卡在当地暂时办不到这项业务。在离境前,我还需要两顿饭钱和去机场打车的钱。 街上的他们 火种源跟着擎天柱到圣地亚哥去调查小商品市场的情况,我们在电话中已说了再见,不好再打扰他了。 上次到哈瓦那来的那个我,在不经意中长了七岁,不会再像油菜花地里的狂犬,我得想办法去挣点钱,好开路! Catedral广场很漂亮,也很有人气,巴洛克风格的哈瓦那主教堂坐落在那里,是一个热闹的景点。 我决定到那里去扯个摊摊卖艺。我没有任何乐器,遇到过的音乐老师都说我唱歌跑调(左嗓子)。我想在这里用中文唱歌,当地人和外国游客听不懂,很难甄别正确与否。就算遇到了内行,又爪子嘛,反正我又不期望走上音乐的康庄大道,只是临时糊下口而已,试一哈。 我在广场边的一个廊角下,用报纸折了一个装钱盒,放在摊位前。然后,我扯起嗓子就开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曲终了,有人围观,但没有人往装钱盒里扔钢蹦儿。 我又接着唱: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我声情并茂、情不自禁地还有肢体动作配合,这时开始有听到有硬(成都音读嗯)币落下的声音了,响了好几次,阴倒在心里默了一下,估计晚饭钱还是不够,还得继续唱...... 几首歌唱完,嗓子就要求稍息。我又开始朗诵诗歌: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面对大海,春暖花开......就在这时,我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一个白人老头,一开始就站在离我不远处,静静在听我唱歌、诵诗。好一阵后,在我唱歌与念诗交替的间隙,他走近问我:你是北朝鲜人吗? 我说:不是,不是,我是中国人。 他克制着讶异?因为当时去古巴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被旅行社安排在海滨的高级宾馆里度假。在街头摆摊的,多半是漂洋过海,刚爬上岸来找兄弟的北朝鲜人。白人老头叫约翰,来自美国加州,是一个"白左"(这个定义不知准确否)。他朝我的装钱盒里放了一张元美金的纸票,元哦!!他问我,有时间有兴趣和他聊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吗?当然,当然可以,就他那张纸票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可以收工陪聊。国会大夏他邀请我到附近一家咖啡屋就坐。喝了一口咖啡后,他便侃侃而谈。他说:我是共产主义拥趸者,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我天天都盼望去北京,把革命的火种接到美国,让它蔓延至全世界...... 可是,你们中国当时不准我去,把门关得紧紧的,认为美国人民都是帝国主义。等你们敞开国门时,你们的国家就变色了,我也没有兴趣再去了......我喜欢古巴,人人平等,大家生活都清贫,彼此没有攀比,也就没有失落,看上去,他们比我想象的开心。 我说:没有失落,会不会是因为他们与外界没有对比?封闭中的人,以为全世界人的生存情况都和他们一样,自娱自乐是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约翰说:只要开心就好,至于什么原因致使人们开心的,没有开心本身重要。他又失望地说:古巴正在消逝,特别是这几年,速度越来越快,即将失去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 我问他:这个独一无二的特色需要多大的代价来支撑?你认为誰又是这个代价的真正支撑者? 他盯着我,不语。停顿一会儿后,他恳切地对我说:讲讲你们中国八十年代前,社会主义的特色?居民区一角哈哈哈哈,我笑着对他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等我们这一代人懂事后,对“主义”些是没有概念、也没有兴趣的。你想了解,我可以讲点我听说的。 他点头,满眼的好奇与亢奋。 我说:听我奶奶讲,在他们那个时期,有些人的老婆和老公是组织上发给他们的(组织介绍)。 我奶奶还差点被组织上发个“南下干部”给她。 后来通过证明,我爷爷在大学时,就确立了和我奶奶的恋爱关系,算是有未婚夫的,才说脱了那个“南下干部”。 那时,房子也是单位分配的,看病也不要钱,实行的是义务教育。组织上对人民无微不至,那么人民对组织也不能有二心,随时要将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向组织上汇报...... 听我妈说,到了她们那个时代,就没有发老公老婆的现象了,但生孩子的数量政府是规定了的,只准生一个......约翰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打着哈哈。 当地居民 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约翰谈兴仍然很高,他建议我们转台去间酒吧继续神侃。我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明天要离开哈瓦那,要早点回去。就这样,我们拥抱再见。我谢谢他对我的支持和善意,他说:很高兴与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希望还能在古巴任何一个城市的街上再见你。 天还未黑尽,我回到了民宿。见到客厅有一对大龄男女在聊天,我以为他们是到游客沙龙来蹭网的游客,没想到他们是冲我而来的。男的叫鲁本,女的叫A,他们来找我的原因是听说H先生家住着一位中国人,中国是道教的发源地。 鲁本和A是以色列人,是对情侣。以色列人大都信仰犹太教,但鲁本是个另类,他信道教,被亲朋好友们视为大逆不道的异教徒,不被大家认同接受。A是他的青梅竹马,两人相爱,又因宗教的纷争一直不能结婚。A甚至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道教,是鲁本妄想出来的。鲁本竭尽全力想证明,世界上是有道教的。 鲁本见到我,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无需更多的言语,便亲切有加。他迫不及待地需要我向A证明,世界上有道教,来源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教”! 我向A点头认可鲁本的说法。 我在上大学时,背着家长,选学一门课程叫禅宗。虽然我不懂道教,但与鲁本一开聊,竟有几分投缘......我们滔滔不绝,谈得甚欢,忽略了在一旁的A。A拧着脸盯着天花板,突然甩出一句:本,你就赶快去娶个中国姑娘吧!然后,冲气往大门走......鲁本赶紧去拉回捹起捹起要走的A。我对他们说:来来来,我给你们讲个中国姑娘的爱情故事。 我来到客厅里那架钢琴前,掀开琴盖,端坐琴前,落指.....《梁祝》的旋律响了起来,这是我的保留节目。A和鲁本安静地立在钢琴旁,听得入神,一曲未完,A已靠在鲁本的臂弯里了...... 我给他们讲了梁祝的故事,一个被“正确”摧毁的爱情悲剧。A泪光闪闪,鲁本搂着她的肩,一副害怕失去她的样子......随后,我们开始天南海北地聊天,其中一个话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关于一份爱、一门宗教、一种“主义”,是否都应该赋予对方或受众体以充分的自由(尽量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 聊至夜深,临别时,他们邀请我一定要去一趟以色列。哈瓦那大学要离开哈瓦那了,想对H先生和太太说些什么。这次到哈瓦那,我带了一些纸张,有时会在房间里记录我行走的流水账。H先生多次看见后,以为我是作家。由于海明威在古巴完成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地人就很崇敬作家。 每当H太太像妈妈一样,在我的房门前嘘寒问暖时,H先生就会很紧张地呵斥她:不要打断作家的灵感,别人正在创作。我对此也没有做过解释,悄悄享受一份假作家带来的虚荣。 临别之际,我想还是应该拿出点与作家身份匹配的东西来感谢主人家。 我决定郑重其事地写一封信给他们。 古巴邮票打开手机的音乐,把纸铺开,高山流水般的旋律,裹挟我的思绪,我听见笔落在纸上的沙沙声...... 在哈瓦那的国营商店,我买了些有古巴特色的信封,准备带回去做纪念。我在其中选了一个图案精美的信封,将我写好的信装在里面,然后朝客厅走去。 在H夫妇面前,我双手呈递我的信,对他们说:这里面盛满我的谢意。 H夫妇十分惊喜,H太太请我为他们朗读一遍。一直以来听到别人朗读诗歌、散文什么的,我就会一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此刻,为表诚意,我必须让自己全身起一盘鸡皮疙瘩。亲爱的H太太、H先生,这次到哈瓦那,你们给了我宾至如归的感动,让我感到天涯海角也有亲人的温暖......(省略)你们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处在艰难困苦中,你们的人民却有着惊人的耐力、勇气和达观,静候着一个崭新未来的抵达。我会深深地祝福你们,在每天....... 听我朗读到这里,H先生周身开始激动,他激动地拥抱着我,H太太也开始激动,她上前来刨开H先生,和我紧紧拥抱,泪流满面......H先生说:哎呀!你的眼泪把作家的体恤衫都打湿弄脏了,松手、走开......为期一周的古巴之行结束了,再见,哈瓦那!再见,H夫妇!再见,未见到的昆多! (未完待续) END闲谭编辑坚持乡土情怀支持闲谭原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dt/5009.html
- 上一篇文章: 游玩玩转儋州的ldquo五一r
- 下一篇文章: 如皋第一家咖啡酒吧,从白天撩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