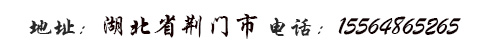林一林,艺术世界中的游牧者
|
“大尾象”成员在“安全渡过林和路”作品实施现场 “他做这个干嘛?”这个问题来自于艺术家与策展人候瀚如的一次访谈,林一林用这个问句来表示他希望行为可以在观众中引起反应并落入思考。这个简单的句子本身包含着一些复杂的意味:行为的目的不是使人为之震惊,因为“震惊”太过强烈和正式,同时具有一种政治化的恐吓(考虑到他行动的起点都与社会政治有关)。于是,林一林的行为更接近于一种“有意味的”行动,意在引发观众神经官能的轻微不适,一种点到为止的提醒,并非激烈的阵痛或矛盾的撕扯。 林一林似乎一直是艺术世界中的游牧者——他的展览履历可以看成是一幅当代艺术的地形图,即使这本身并不值得炫耀,但是在这一次次地点的转移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创作的路径和方式:大量的创作与实践都是在参加驻地或艺术基金会组织的项目中完成的。这些项目能够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当地状况,避免了长期生活于一地所形成的狭隘与偏见。全新的环境对个人的旧有经验提出了质疑,迫使身体内部的经验或参数不断调整,要求他再次确认其对认知的判断和对艺术行为的认识。机遇和情境构成了林一林独一无二的思考与创作语境,成为新作品的起点和条件。由此看来,作品反倒成了一个次要的概念:无非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之确立的一种记录,重点在于一种不断产生的测试关系,或者说,“临时的共同体”——这是由艺术家创造出的“变量”在整体系统中运行的过程。 除非能够策略性的成为一个项目可以进行深入测试的“变量”,否则,他的亚洲移民身份也就不显得多么重要;他的“金色”系列作品中使用到的中国元素,仅仅是因为“很偶然在路上碰到舞狮队的老板”①,随后他进一步解释道,“其实我并不太关心这种中国元素里边的文化含义,我觉得我是很自然地在用它。”② 金城,,行为,60分钟 在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他成为古巴馆的参展艺术家之一。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又成为志愿社工。现在他每年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北京教书,另外的几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区穿梭、游历、创作。事实上,他的身份始终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中:西方/非西方、有国籍者/跨国籍者、职业/无业游民、专业/业余……多重且不确定的身份,导致了他对“艺术家”身份认识上的更新——既可以是任何身份,又不是其中任何一种。艺术家的身份首先就成为职业分类中的一个不可描述的“变量”,在既定的社会网络中,其生成与书写关系是“根茎”状的、不断延展的。譬如,他在温哥华唐人街小巷的行为表演《形象知识学》中,他究竟是社会学者,颅相学专家,建筑学者,考古学导师,亦或是泄密者?他为何这般故作神秘,招摇过市?这一行动性质为何,意义何在,竟至于不惜将自己置于如此的险境之中?细想起来,唯有这一混杂而暧昧的“临时身份”,才能将他的多重兴趣与当地状况复杂不安局势结合起来。 如果说艺术家的身份成为这样一种跳跃性的“变量”的话,艺术的任务应当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输入一个同样不确定的“变量”。早在“大尾象”时期,该团体就已经在针对特定的语境创作了。他们独特的判断方式以及“街头游击战”式的展览方式,都明确指向了在情境和机遇中创造艺术的观念。“变量”的引入,是对作为“常量”的整体社会语境的不满,并积极的引入一个活泼的未知数值,成为一种产生(临时性)方案的因子。因此,无论某个“变量”与环境的耦合方式为何,其不确定的值,产生了持续的批判效应,其价值也在特定的区间中波动。这样,无论是作品自身的完成,还是预留给观众的空间,都是开放性的:一方面,作品的结局开放而未知——既有可能因为触发了社会的敏感神经而导致“测试行为”的终止,也有可能顺利按原计划完成;另一方面,观众获得了选择的自由——或者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或者参与、介入其中。从这一点上来说,林一林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传统的身体政治美学范式之超越,而将“变量”引入到社会批判的维度之中,已然是系统美学(以及作为其子嗣的“关系美学”)的一部分。持续性的单一动作的重复,不是对身体耐受力的极限评估,③,而是对社会进行持续测试的艺术的方式:保持个体“变量”的可识别性,以累积的方式使社会“常量”获得重新定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dx/1281.html
- 上一篇文章: 潜点哈瓦那,等待世界已太久
- 下一篇文章: 第二梦想号抵达马达加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