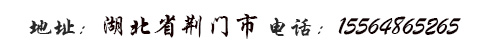环游世界后的人在做什么
|
在彷徨,在疑问,在蜕变,在失去,在获得,在时间和空间里流浪。 我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在一个西部的省会城市长大。 家里的亲人大多是教书匠和医生,小时候从来不敢跟班上那些赚了钱,买完文具买衣服,买完衣服买老师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比逼格,也更没有机会接触什么机关大院里的达官显贵。家里有一个书房,里面是爸妈读大学,做大学教师时看过的书,书皮上那些名字,我记得有巴尔扎克、雨果,有荷马,有莎士比亚,有海明威,有契科夫。 懵懵懂懂中,就从这些书里,知道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是灰墙巴洛克、阳伞咖啡座。可是这只存在于脑海里,图片里,文字里。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不像北上广那么摩登,但是自古以来算得上惬意和宜居,优雅和时尚。 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只要活在这里,娶个媳妇成个家,打个麻将喝个茶,整个世界我都不想去了解,似乎到死我都不想走出去。第一次出国,是在我19岁那年,不是我心存向往,而是走投无路。 告别病重在床的外公,告别已经见过家长的女友,一个人去到地球背面。 我去的第一个国家,SH主义古巴。 当时,在我的想象里,这里和刚果、朝鲜、阿富汗,就是一个概念。大概就是满街的扛着RPG的黑人,用棕榈叶子搭建的房子,街上TOYOTA皮卡开过,卷起一阵红土......如果不是国家公派,有协议再先,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敢,也不想走这一趟。去古巴,要从法国转机,当我降落戴高乐机场的时候,飞机从跑道滑向候机楼用了半个小时,同学开玩笑说——坐着飞机逛巴黎。我看到外面跑道上的飞机排得像我家乡的交通干道上的的士,密密麻麻,几十秒起飞一架......进入候机楼,只感觉这里特别的安静,也特别的干净,空气中好像没有太多活跃的分子,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梦游。后来每年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环球飞行,无数次路过戴高乐、史基浦、法兰克福、巴拉哈斯、浦东、首都机场,竟好像是出门赶个地铁一般随意。 已经记不得是多少次从这里出关...... 原来戏谑说人家的校车是福特,我们的校车是-。随着里程数的积累,从最后一排,到经济舱舒适座,到商务舱,到头等舱,先先后后坐了个遍。 第一次从欧洲飞拉美的飞机上,航空餐里有法国烤圆面包,波尔多,卡门贝干酪,这些都是以前只听说过的东西,用餐时,空姐给提供了一瓶很小的橘黄色的饮料,我以为是橙汁,一饮而尽,然后被这朗姆醉到飞机降落。哈瓦那的机场确实很小,我甚至怀疑飞机会不会被它那不平长草的跑道磕坏了轮子,唯有那停机坪上维珍航空的硕大的尾翼,远远地映入眼帘,给人少许安全感。来迎接我们的是穿戴整齐的小学生,这个国家很穷,但是,人人都很干净症结。 然后随着我们在这里生活,慢慢才知道这里有15世纪的城堡,16世纪的宫殿,17世纪的教堂,18世纪的别墅,19世纪的酒店。 才知道,这里不是沙漠,不是丛林,不是农村。 有这个—— 有城市—— 有这样的海滩—— 有这样的晚霞—— 这里有《摩托日记》里那个充满理想的切?格瓦纳—— 有燃情岁月,有20世纪最后的将列强戏弄于股掌之间的战士—— 还有一群礼貌文明,又热情奔放的人—— 这些是曾经教我语言的老师。 逐渐理解海明威,体验着他喝着邰吉利,抽着雪茄,酝酿着巨著,扣着诺奖的感觉—— 这里走在路上,人和人见了面,要友好的打招呼,这里到了晚上,有各种各样的PARTY,聚会。好像并不是长辈们说的那样——无非就是七十年代的中国。 我曾经住在一个叫塔拉拉的小镇的海边,四年。 记得宿舍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宿舍的一头,是金色的沙滩,另一头,是起伏的山丘。 切·格瓦纳的别墅就矗立在山丘之上,旁边有颗合欢树,每到春天,树上会开出一串串风铃般的金色花朵,远远望去,格外耀眼。 半山腰,有座上个世纪挖掘的海防地堡,里面容得下一门加农炮,如今火炮已被拉走,只剩下掩体上的几棵椰树,还像哨兵站在那里眺望。地堡旁边,有一座预制板搭建的舞台,如果挂上幕布,整个海滨就成了一座露天影院。舞台旁有一条行人踏出的小径,弯弯曲曲连接了海滨低地与山坡上那条名为海豚大道的混凝土公路。 蓝天为幕,缓缓飘动的白云下这座好似宫崎骏漫画中的山丘,总是让人充满向往,因为是迎风坡,山丘上的草总是长得格外茂盛,海风吹来,摇曳摆动,泛起阵阵绿浪。 在齐腰深的野草中行走要格外谨慎,因为脚下的碎石间,掩藏着海鸥的窝巢,里面时常会有一些尚未孵化的鸟蛋和刚刚破壳的幼崽不堪惊吓。 我曾经坐在金合欢树下看日出——清晨的海滨格外安静,西梅克斯集团送餐的面包车静静地驶过护士站,拐个弯走向食堂,远远的海平面上游轮驶过,示航灯一闪一闪,忽明忽灭,然后天际开始泛白,发黄,一轮红日羞羞答答又迫不及待地爬上来...... 我曾经躲在切·格瓦纳别墅的屋檐下观雨——那场面恐怖而又恢宏,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鸣,惨白的闪电撕裂夜空,黑色的水天大幕衬起魔鬼指挥的交响曲...... 我曾经和吃货一起,拿着刚发的土比索,去山坡那头的“谐和”咖啡馆买炸面团、烤鸡腿和冰番石榴汁。 我曾经无数次一个人在午夜走下这山坡,悄悄溜回沉睡的宿舍。 我曾经想要在这棵金合欢树下做一个秋千给自己心爱之人,却迫于距离,未能实现。在加勒比,我曾经坐过仿佛是装伞兵的上了天就下不来的飞机跨海飞行—— 看不到几个窗户,舱顶上冒着白雾,送水的是黑哥哥,但是据说飞行员是军航,开得特别稳。然后我们看到大海像镜面一样反射着阳光,在云层间的缝隙里忽隐忽现。看城市上空笼罩着乌云,暴雨倾盆而下,那时感觉自己好像上帝一样。 在加勒比,我迎接过自己国家的海军舰艇初访,看到国宾级的仪仗队。 记得当舰艇要离开的时候,两个国家的军乐对一个在岸上,一个在舰上,互相对奏军乐,一支又一支,然后船只鸣笛告别,那种气势,就是“沙场秋点兵”所描绘的,真的让人心潮澎湃。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世界特别特别大,我们所听说的那个世界,或许只是听说的,是某些人要你知道,规定你知道的。而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后来,我来到了欧洲,先后去过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梵蒂冈、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希腊等,也曾踏上过非洲大陆。七年来,跨越四大洲十多个国家多座城市。有些时候是和朋友一起,有些时候,是自己买了打折票来个短途游。一块去旅行。但是因为我是个相当宅的人,所以这些旅程多是自愿的少,被鼓动的多。可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三五天的经历,会留下一辈子磨灭不掉的记忆。 你会从地图上去考察一座城,从别人的语言文字中,去发掘它的亮点,然后跋涉千山万岁来到它跟前,呼吸这里的空气,摩挲这里的草木,端详这里的建筑,倾听这里的历史。然后它就会住进你的生命里。塞戈维亚,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只知道它这里有白雪公主城堡的原型,如果不是熟人指点,根本不晓得它后面还有这样一条仙踪小径。当时大家走累了,坐在一片草坪上,看遛狗的情侣,看风吹叶黄。 我研究生阶段的外国导师说,要了解西方的文化,你需要去三个城市,它们是罗马、雅典和耶路撒冷,而他最钟爱罗马。 在这个满地都是文物的城市里,在罗马市苑的废墟,在西班牙广场,我第一次感悟,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底蕴,不单单是用繁华和现代化就可以衡量的。那种千年积淀下来的厚重,不经意流露在街头巷尾的散漫之中,伟大二字的冲击力,好似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在这里邂逅和寻找《罗马假日》里的奥黛丽赫本 不住要去想,为什么在罗马的地名要叫西班牙阶梯。直到一点一点搞清楚,原来西班牙使馆在这里,处处留心皆学问。 佛罗伦萨,当时一路的朋友硬要去体验一家正宗的意大利餐厅,我觉得很不以为然,觉得景点不过都是宣传,结果到了门口一看,居然还要排队。门面超小,态度也超屌,越是这样,就越不甘心,一定要试一下。进去了才发现,这里挂了一墙的照片,有球星,有帕瓦罗蒂,有总统。最关键的是,并不贵的价格,却吃得相当地道。 然后深夜里又和摄友游荡到城市背后的高地,看着这个百年古城在夜色中睡去......在我的家乡,没有这样安静的画面,这画面的城市中,也没有几个拥有几个世纪历史的老建筑,作为一种灵魂或者象征,显赫而骄傲的占据一方。 回酒店的路上,遇见小猪喷泉,我想起这就是小时候自己在《汉尼拔》里面看到的,帕奇督查洗手的地方,现在,它就这样触手可及! 在梵蒂冈,亲眼目睹教皇的真容,在圣彼得大教堂穹顶上数圣象—— 瞻仰米开朗基罗的签名真迹—— 和拉斐尔展开穿越时空的对话—— 一睹传奇的瑞士卫队风采—— 在米兰,瞻仰最后的晚餐,还有几百年前拿破仑加冕时站立的那块砖—— 在日落时分爬上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塔楼,四个大钟一起敲响,然后天边慢慢从白变成蓝,变成粉红,变成黄....... 然后当你穿过叹息桥的时候,你会想起那个关于情侣接吻的故事和莎翁笔下的《威尼斯商人》。 圣托里尼,小时候只有在晨光的笔记本封面上瞻仰的地方。 还记得那是在捷克,为了看一眼夕阳,我爬上了天文钟钟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这一生没有遗憾了—— 这里没有什么许愿池,但是有在查理大桥上殉难的圣徒,有卡夫卡、米兰昆德拉。 库特纳霍纳,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说,中欧有一所恐怖的人骨教堂,那时候好好奇,连续几天睡不着觉。而现在它居然不再是一个地标,一个符号,一张照片了!于是我们试着用GOOGLE把它找出来,然后辗转前往,墓园很小,却安放了上万具尸骸,看书和亲自走进那个地窖的感觉太不一样。站在地库里,头一次感觉到脊背发凉,但是不晓得这种感觉,叫不叫酷—— 从阴森的地窖出来,看到复活节前后来墓园祭扫的东欧人,里外两个世界差距是那么大,看到大理石板缝隙里爬动的甲虫,老是会去思考,生死是非常现实却又飘渺,严肃而又幽默,沉重而又轻松的事。里斯本和辛特拉是我一个人去的,坐了一个晚上的夜车,然后大清早起来,从火车站步行到酒店,一路经过贸易广场,经过圣乔治城堡,经过流浪者大街,你晓得你不属于这里,所以每分每秒都好像是借来的,你可以看到的,可以触及的一切,都是珍贵的。因此,目光和脚步格外流连。 路过海军博物馆的路上,看见很多人在一个小店排队,仔细一看招牌是贝伦糕点。早就在很多国内的网上看见人们把这里吹得神乎其神了,也经常看到各种餐厅打出正宗葡式蛋挞这样的招牌,虽然我特别鄙视装逼和赶时尚,对甜点也没有什么研究,但是看到很多欧洲人都在排队,还是鬼使神差的凑上前去—— 因为不是很喜欢打挤,我是坐在路边啤酒馆的折叠桌边尝试这传说中的神物的,第一口给人印象深刻,表层有张力的糖浆,内部酥软的蛋芯,像龙眼酥一样层层酥脆,一咬下去就化开的外壳,然后填满整个嘴巴的浓郁的香气,让你不得不折服。 到里斯本必须要寻找两个人,一个是恩里克王子,一个是古本江先生。故人未远,在这座不大的海滨城市,处处都有他们的踪影。虽然一个生活在古代,一个生活在现代,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客人,身份差异是那么的明显,但他们却用自己生命的不凡之举表现出人性中最光辉的执著与无私,共同铸就了这座城市,乃至于这个国家文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也在全人类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品尝过百年老店香酥甜美的正宗葡式蛋挞,沿着已被岁月打磨成光滑骨牌般碎石铺就的小路,乘着叮当作响、摇摇晃晃的老电车穿行于街头巷里和码头海滨,不难领略圣·乔治城堡的高傲、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华丽、热罗尼莫斯修道院的神秘、商业广场的宏伟、贝伦塔的精致,可是驻足于大航海时代纪念碑脚下时,真正的震撼却无以言表。 年,葡萄牙人民为纪念航海王子恩里克逝世周年以及葡萄牙开拓海洋的辉煌历史,在茹特河畔树立起一座面朝大海的石碑,其外形如同一艘乘风远航的大船,气势恢宏,站立在船舷的人物雕刻栩栩如生,船头是恩里克王子,手握模型帆船,抬头远眺,两旁身后是航海家、将领、造船工匠、传教士和科学家。不同角色,不同职业的人,在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带领下,共同托举起向海洋进发的梦想。 15世纪上半叶,葡萄牙航海发现取得的成就震惊欧洲,这和恩里克王子的坚毅密不可分,他亲自参与了帆船的改进,广纳良才,在萨格里什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航海学校,教授航海、天文、地理知识。随着一次次理论知识的进步,葡萄牙人在海洋上越行越远。年,当王子谢世于他的航海基地时,生活简朴,终身未娶,却已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探索事业,从此,每一个从事地理大发现的人,都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 多年前,海洋对于人类来说,神秘、险恶却又充满了诱惑,水天之际,视野极限,究竟是丰饶之地,还是万丈深渊,仅仅只能凭借这个位于欧洲大陆边陲的弹丸小国用几只木船、数片孤帆去验证。年,当阿姆斯特朗代表人类登上月球时,他知道身后是上亿人期待的目光和无数精英科学家的全力保障,而古代的水手们却仅能依靠有限的经验和无畏的勇气,沐浴暴风骤雨,饱受风浪颠簸,向未知世界发起挑战。眼前这座纪念碑就像一座祭坛,所供奉着的不仅仅是一尊尊人像,不仅仅是在惊涛骇浪中献身的壮士,而是讴歌着全人类勇往直前、求索奋进、挑战极限的进取心。 如果说恩里克王子带领葡萄牙人民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航海史,奠定了这个民族迈向世界的硬实力,那么一份意外的馈赠,则为这个国家注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儿时阅读《行者无疆》,余秋雨先生写到葡萄牙时惜字如金,却浓墨重彩地缅怀了一位英裔土耳其人——卡洛斯特·古本江。这使我好奇究竟是何许人能引得作者如此白癜风中医哪家白癜风好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dx/560.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闻早餐2017年9月2日
- 下一篇文章: 龙应台一个再也不打开的抽屉飘零的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