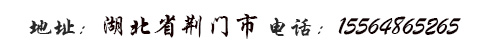哈瓦那已不再是世界边端,你甚至可以去古巴
|
▲去古巴消磨时光。 他明白他如今终于给打败了,没法补救了,就回到船梢,发现舵把那锯齿形的断头还可以安在舵的狭槽里,让他用来掌舵。他把麻袋在肩头围围好,使小船顺着航线驶去。航行得很轻松,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此刻超脱了这一切,只顾尽可能出色而明智地把小船驶回他家乡的港口。 一切仿佛风平浪静,我仍为之前老人与海激烈搏斗的片段久久无法平静。 坚硬有力的海明威,一生浪漫传奇,每年从1号公路驱车前往佛罗里达州最南端基维斯特(Keywest)寻访其足迹的游人络绎不绝。 ▲古巴乐手在夕阳西下的哈瓦那马雷孔(Malecon)海滨大道演奏。(图/新周刊) 此刻,作为海明威迷的我,在距离基维斯特仅公里、相隔一条佛罗里达海峡的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硬汉如他,固然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但让海明威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却有赖于古巴的滋养——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断断续续在古巴住了三十年。古巴老渔民富恩特斯搭救了暴风雨中沉船的海明威,富恩特斯出海捕鱼的真实经历也成就了海明威。 站在哈瓦那北边的马雷孔(Malecon)海滨大道上,看着海浪猛烈地拍打着腐朽发暗的石壁护栏,海水飞溅到街道上,甚至漫入城区,往更深的地方侵蚀着这个古老的城市。夕阳西下,古巴人所称的“北风”(LosNortes)穿过我的T恤,窜入我的身体。 我想象这个国家的前世今生,它早已不再是世界的边端。 ▲哈瓦那附近的海玛尼塔斯,大人收拾渔具,一旁的孩童在海水中玩耍。(图/新周刊) ●●● 梦想着像雪茄一样“走私”到美国 “Hello,Havana.”年3月25日,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以这句问候拉开了哈瓦那演唱会的序幕。大约有50万人从古巴各地以及其他国家赶来,见证了这场历史性的演唱会,包括我。 “时间改变了一切。”米克·贾格尔认为这场演出如果在10年前举办,将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而现在,古巴人似乎马上就融入这场欧美式音乐节的狂欢,他们熟悉滚石乐队的音乐,举着滚石乐队的“大舌头”标志,身体自然而然地跟着音乐跳起来,仿佛这种音乐、这种生活、这种自由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 ▲哈瓦那滚石演唱会现场。(图/大家) 这次旅程认识了年轻音乐人EdgaroGonzalez,他从小住在哈瓦那城东北的阿拉马(Alamar)离美国佛罗里达更近,近到他拿着收音机站在楼顶便可以收听北边的“敌台”。 在他小时候的上世纪90年代,Edgaro成了“声名狼藉先生”的忠实粉丝,他听着美国人的音乐学会了英语。近年来,Edgaro开始与同伴玩雷击顿音乐(Reggaeton),引领了一场朝气蓬勃的社会运动——古巴所有年轻人都在听雷击顿音乐。 ▲哈瓦那附近的海玛尼塔斯,一名身穿美国星条旗短裤的古巴年轻人,在一个垒球场上遛狗。(图/新周刊) 古巴政府当然想遏制它,然而这股潮流就像吹彻古巴的北风,不但无法驱散,也无法离开它。肯尼迪总统年签署了对古巴禁运法案,但古巴雪茄仍然源源不断地走私到美国。雪茄销往美国,暗藏着古巴民众的“美国梦”——梦想着像雪茄一样“走私”到美国。 ●●● 古巴无法把“美国”从这个岛屿上抹掉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古巴可以分为“有美国亲戚”和“没美国亲戚”,或者美元和古巴比索两个世界。我所居住的马雷孔大道上的里维拉酒店,就是这种分裂的典型代表,豪华大气美式建筑在楼房低矮、街道朴素的城市里显得格格不入。 革命前梅耶·兰斯基企图在这里复制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传奇,把这里打造成拉丁美洲最大的赌场饭店,让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在古巴赌一把。革命后,美式的管理制度随着美国人的离开而消失,当我走进酒店,充满官僚气息的服务水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这里是社会主义古巴。 ▲正在修缮的古巴国会大厦,哈瓦那街道上古董汽车、三轮车与马车齐头并进。(图/新周刊) 即使如今古巴的正统史书把美国控制下的古巴共和国时期称为“伪共和国”,那50年被形容为“纸醉金迷的50年”,古巴政府也无法把“美国”从这个岛屿上抹掉——除非他们把一切建筑铲平,让古巴变成一片废墟。 在哈瓦那旧城,有一栋著名的建筑——百加得大厦。年,这座大厦建成时是哈瓦那城最大、最豪华的建筑。而彼时哈瓦那港的西岸是拉丁美洲最繁华的地区之一,满大街跑着最先进的福特、雪佛兰或奥斯莫尔比等牌子的美国汽车。70多年后风光早已不在,这些已经成为老古董的汽车依然在哈瓦那城跑着,让一些游客发出小清新的感动:“时光在这里凝固了。” ▲卡萨布兰卡的耶稣像。(图/insidethevatican) 从旧城乘渡轮,往莫罗三皇堡的方向前行,山顶高高的灯塔越来越近。船靠岸后沿公路徒步上山,哈瓦那港湾那片广阔的大海被抛在了身后。到达山顶,一尊大理石耶稣雕塑矗立,这个地方叫做卡萨布兰卡,就在百加得大厦对岸,哈瓦那港的入口处。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驾船开入哈瓦那港的时候,远远地便会看到这尊高达20米的耶稣像站在古巴入口处,欢迎他们的到来——让人想起站在纽约港口向各地难民振臂一呼的自由女神。 ●●● 古巴确实不再孤独了 古巴对美国的迷恋不是单向的,美国人同样对古巴充满了想象。专栏作家安裕说,美国对古巴的迷恋有两个向度,一个是海明威的古巴,一个是白宫的古巴。白宫把古巴看作待拯救的沦陷区,以及必须重新控制的敌占区;而在左翼青年那里,古巴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国度,是他们在资本主义霸权下朝思暮想的乌托邦。 长久居住在古巴的海明威,在这里过着创作者梦寐以求的生活,休闲而孤独:“那儿有无穷无尽长的沙滩,硬邦邦的白沙,二十里内渺无人烟。我们白天出发,在海上晃荡,有时跳下去游泳,在晚上的某时某刻返程。可能在船上睡觉。也可能在城里睡觉。”我在久负盛名的“街中小酒馆”中歇坐,墙壁上满是顾客签名和留言,其中不乏一些名人政要,而唯独海明威,这位美国大文豪的留言始终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奥比斯波街上,一家商店的橱窗贴出了美国明星茱莉亚·罗伯兹的广告照片。(图/新周刊) 上世纪60年代,古巴新政府成立后,欧美的左翼青年纷纷到古巴朝圣。“革命是一剂猛药”,这是萨特对古巴的观察,他认为古巴对制度的推倒重建“必须经常与暴力相伴”,但他并没有对这种暴力进行道德批判,就像他对苏联集中营的沉默一样。 萨特和波伏娃从古巴回来后,便热情地向西方赞美这片革命中的国度。倒是马克思主义期刊《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的编辑胡贝尔曼和斯威齐保持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他们颇有预见性地指出:“一场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今天看来整个的事物到了明天可能就不正确了,反之亦然。” ▲哈瓦那科希玛渔港,海明威经常在这里出海钓鱼,码头边有一家“LaTerraza”餐厅,海明威在那里结识了《老人与海》中老圣地亚哥的原型人物卡洛斯。(图/新周刊)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古巴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古巴不得不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旅游业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街头开着一辆破车的出租车司机,其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高十倍。 当年1月,教皇约翰·保罗赴古巴参观访问时,这位古巴皈依天主教年来第一位访问古巴的教皇,在离开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在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生存。”同年,维姆·文德斯用录像机记录了古巴音乐最后的余晖,爵士音乐人欧玛拉和伊布拉印的对唱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 ▲哈瓦那老城中的圣克里斯托尔大教堂外,一位抽着雪茄的古巴男子。(图/新周刊) 可惜的是,旧的古巴最终会随着这些爵士音乐人的逝去而沉寂,新的古巴将是美式音乐的天下。在美国风潜移默化下长大的古巴年轻人,无疑会对当前的趋势表示欢迎。今日古巴与美国恢复建交,Airbnb成为第一家入驻古巴的美国互联网公司,给这个岛国带来了互联网共享经济。古巴确实不再孤独了,它将被世界共享,希望也能共享世界。 ▲维姆·文德斯的《乐满哈瓦那》中,老乐手向世界展示了古巴音乐伟大的根源,令世界掀起古巴音乐热潮(长按扫描北京治疗最好白癜风专科医院小孩白癜风可以治好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dx/636.html
- 上一篇文章: 周末浪人夏日冻龄计划
- 下一篇文章: 哈瓦那一个可以停下来和自己的灵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