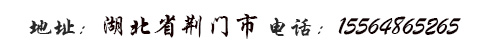邱华栋所有优秀作家都在共写人类文学这本大
|
/访谈者简介/ 邱华栋,著名作家,文学博士。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5岁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等12部,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楼兰三叠》等30余部,以及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等多篇。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韩、俄、英、德、意、法和越南语发表和出版。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北京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人民文学》林斤澜小说奖等。现居北京。 ——邱华栋访谈录 邱华栋/张英 #我觉得激情来自生命的本能# 张英: 记得我们在大学读书搞文学社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后来你开始写小说。现在,你的小说实力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公认。年你五十岁的时候,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38册的文集,有万字,很让我惊叹。我回想了一下,从大学时候和你相识至今,快三十年了,当年那么多喜欢文学的朋友,到现在还在坚持写作的人,真已不多。至今我们在一起还能够谈文学,更是不易。你现在还写诗吗?邱华栋: 诗还在写,只是从创作数量上讲,比以前要少得多了。诗很重要,对保持良好的语言敏感度是非常有帮助的。尽管我现在诗写得少了,但一直在写,并没有中断,也出了好几本诗集。年4月还出版了诗集《编织蓝色星球的大海》,大都是二三十岁时写的,精选了一百多首。 我写诗开始得很早。中学生时就开始写,算是年代的校园诗人。除去唐诗宋词对我的早期影响,现代汉语诗对我最早发生影响的,应该是“新边塞诗群”的昌耀、周涛、章德益、张子选等。接着,我读到了“朦胧诗群”诗人们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舒婷的诗。上了大学之后,我读了现代诗人们的作品,如胡适、卞之琳、冯至、闻一多、郭沫若、朱湘、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王独清、艾青等诗人的集子,大学的课程有关于他们的研究。上大学之后,写诗比较多。当时,武汉各高校的校园诗歌活动很热闹,武汉大学有出诗人的传统,像王家新、高伐林、林白、华姿、洪烛、李少君、吴晓等。 早期我出版过两本薄薄的诗集,是年的《从火到水》、年的《花朵与岩石》,收录了早年的诗歌;在年出版了诗集《光之变》,我还自印了两册诗集《情为何》《石油史》。后来又出版了诗集《光谱》和《闪电》,这些诗集的发行量都不大。 可为什么我要一直坚持写诗?诗是语言的黄金和闪电,写诗总是能够锤炼语言。写诗、读诗,能够保持对语言的敏感。人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语言的魔力。诗就是这样,我开始接触文学就是从诗歌开始的,诗的特殊性在于浓缩。浓缩到了无法稀释的就是诗。我总是在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读诗,以保持我对语言的警觉。我希望我的小说有诗歌语言的精微、锋利、雄浑和穿透力。诗歌和小说的关系是这样的:伟大的诗篇和伟大的小说,只要都足够好,最终会在一个高点上相遇。 张英: 你的作品里,有一种强悍的元气和激情,而且从头到尾都贯穿其中,这在今天的小说家里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这种激情在长期的写作中会逐渐丧失,你是如何保持这种激情的?邱华栋: 我觉得激情来自生命的本能,天生的。我从小在新疆长大,那里天地开阔,野马奔腾,天空蔚蓝,碧绿的青草和五彩的野花蔓延到天边,一望无际的金色的沙漠、黑色的戈壁在天山的衬托下闪耀着美丽的光芒,成群的牛羊和茂密的果园在河流边自由地生长,美丽的姑娘和强壮的小伙子在夕阳来临的时候会弹起冬不拉唱歌跳舞,一切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那种环境里我像一棵树自由自在地长大。 我父母是支边青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去的新疆,是新疆交通厅所属单位职工,新疆好多公路都是我父亲工作单位修的。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坐推土机修路,冰大坂上的雪有三米厚,把路全部掩埋了,少年时代,在雪山上,推土机推出很多死羊,埋在雪下……印象非常强烈。 我生活的城市在天山脚下,是个小城市,离开城市骑着自行车往山里走一段,就会发现很好的牧场,高中的时候,我跟一帮同班同学骑自行车,沿着一条河一路走,就到了天山的深处,夏天用手摸着冰雪了,还看到远处棕熊抱着树看着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时,走到了一个废弃的古城,不知道多少年前西域少数民族留下来的,黄昏的时候,夕阳特别美,从古城里飞出来几万只野鸽子,把天空都遮蔽了。 我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少年时期。年春天,我买了一些文学杂志,有新疆昌吉州文联办的《博格达》,还有《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青年作家》《青春》等,当时,我贪婪地闻着杂志的那种油墨香气,感觉到那年的春天正在迅速到来。杂志上油墨的味道是那样好闻,那可是文学的味道啊,使我的内心激动无比。十几岁的少年,还写不了太深的东西。当时的小说,都发表在《语文报》《中学生文学》《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杂志上。 我参加了当时的校园诗歌写作大潮。那会儿我每天写五六首,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写诗,数学成绩不好。我想我就是形象思维、想象力发达。 18岁的时候,我出了一本小说集《别了,十七岁》。当时靠着文学特长,我被破格录取上了武大中文系。在大学的时候,感觉教材比较陈旧,我经常去图书馆读书,和同学成立文学社,写诗、写小说,模仿一些大师的作品,这样就打下了写作基础。当时武大的文学活动很多,有一个珞珈诗社和一个浪淘石文学社。有一个有名的樱花诗会,有一条很漂亮的樱花大道,每年三月、四月份,开的全是樱花,我们就在樱花树下开诗歌朗诵会。我们组织了很多诗会,把武汉各个高校的校园诗人弄到一起朗诵诗,然后评奖。 我在大学里大量阅读,被不断滋养和提升,后来又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三十年里写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写作主要是内心的需要,通过写作,不断发现我自己,表达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 #一个作家必须要有基本产量# 张英: 有人说你作品写得太多,这是个含蓄的提醒:多了未必好。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邱华栋: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我是一名年轻的老作家,每年的产量都很固定。我的写作是属于慢慢爬坡上坎的那种。 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十多部,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描写当代北京城市生活变化的《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另一个是历史小说系列《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以及描写成吉思汗在中亚和中国著名道人丘处机会面的历史小说《长生》。另外,还写有《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闯入者》《4分33秒》《塑料男》等28部中篇小说,大都书写了都市经验和个体生命的生长。还创作有短篇小说系列《社区人》《时装人》,以及系列小说《西北偏北》。当代题材的写作使我有一种“与生命共时空”的感觉。历史小说写作,则需要展开对历史的想象,这都很有趣。 我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有基本产量。写得多并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有进步,越写越好,有变化。我感觉我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个作家一生可能只有一两部代表作,其他作品全是铺垫,每个作家都有量的定数,但多写了,杰作才可能写得出来。 张英: 看你早期的小说就像看我自己的成长,特别亲切。从大学年代写的《叙述草莓山坡》《前面有什么》,到你来北京写的《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还有“社区人”系列小说,对于漂泊到北京闯荡的人来说,这些小说里人物的经历,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这种感动和激情,是别人无法体会的。直到现在,仍然是你的文学最亮眼的坐标,如今回头看这组小说,有什么感受?邱华栋: 我想,你所说的那种感动,还是来源于生活和我们的经历本身吧。一个人从学校毕业,来到大城市工作,那是一个人独立面对生活考验的开端,像是一棵树脱离了苗圃,进入森林里,你必须面对生活的考验。在城市中不断进取,也遭受挫折,是生活经历本身给了我丰富的写作资源,北京对我的生命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我开始和我的作品一起慢慢长大,逐渐成熟。我开始的一些作品,就是对那段生活的记录与思考。那种成长中的激情和寻找一直伴随着我。我笃信“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出发的地方”。因为新闻结束以后,小说家开始进行沉思,进行审美的积淀,用文学审美的形式赋予它更长久的价值。 从年到年,我写了由60篇短篇小说组成的《社区人》系列,以《来自生活的威胁》和《可供消费的人生》为题出版。我将我的目光聚焦到郊区中产阶层的生活社区,这60篇小说基本是写实的风格,但也有部分是变形和夸张的。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系列。 《环境戏剧人》写了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我觉得艺术家是人群中特别敏感的一些人。我的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都是这个题材。然后,我年开始写长篇小说《正午的供词》,在这部作品中,从形式上用了十几种文体,剧本片段、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糅合在一块,虚构了一个电影导演的一生,我拿它来告别我的三十岁。 张英: 你这三部小说有没有整体的思想、意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白昼的喘息》好像是作为中篇小说发表在《花城》杂志上的,它和《城市战车》有什么区别? 邱华栋: 在《花城》上发表的那个中篇是《城市战车》的主要部分。《城市战车》就是《白昼的喘息》。当时,大学生毕业以后来北京的,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好多都是来闯世界的,我和他们有些接触。这三部长篇小说写了七八年,我想让读者能够通过我的小说,感受到整个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和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中国城市的发展逐渐成熟,人们的思维和习惯也比以前要活跃得多,在这样变革的时代环境里,一代年轻人渐渐长大并且老去。 张英: 对于城市,好多老作家都显得不适应,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新的一代人的成长,到了他们的笔下,城市文学才可能真正成熟。 邱华栋: 现在中国有七亿多人生活在城市里,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多,未来会提高到百分之六七十。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其实只存在一种文学,就是关于人的文学,关于人的心灵在时代和历史中的变化。城市文学是一个非常小的概念,什么城市文学、金融文学、女性文学等都是小标签。文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关于人的文学,人要通过文学来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我早已逃离城市文学这个概念,城市的符号,表面浮华都消失了。你只有看到一个人心灵的成长,才会越来越贴近文学本真。 张英: 你如何看待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 邱华栋: 假如写短篇小说如同打造锋利的匕首,那么,写长篇小说,犹如攀登高峻的山峰,或者,好的长篇就像耸立在那里的山峰。在我看来,小说的结构和叙事艺术,是一部长篇最重要的地方。从我个人兴趣而言,我喜欢一种繁复的美学,比如《正午的供词》这部小说,就是我的这种艺术追求的反映。我使用了大量材料,对文体和语言进行很多实验,从而搭了一个小说的积木、一个庞大的建筑。这于我也是一种全新的写法,从这部小说的外部来看,它像是一部犯罪小说,从小说的内部来看,它又是一部大胆的先锋文学、实验文本,显得气势宏大、人物众多,在小说里我一共写了快80个人物,试图通过一个故事去展现生活和人物内心的复杂性,把握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人的内心世界。 另外,这也是一次针对文学史的写作。我们熟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意识流到结构主义,从象征主义到荒诞派,我在小说中再现了这一过程,也算是一种解构吧。我对这些年中国艺术发展事件,比如80年代的先锋艺术热、王朔热、汪国真热等事件和人物都进行了勾勒。我还在语言上进行了各种实验和尝试。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很少有作家利用活生生的语言去写作,比如日记、书信,新闻通讯、特写、传真、档案等,用这些文体去写小说,特别有意思。 张英: 《正午的供词》这部作品摆脱了靠个人生命体验去写作,在小说空间上大大扩宽了写作资源,这种转变是基于哪些想法? 邱华栋: 30岁以后,我的写作不再是青春的燃烧,不再是诗意的吟唱,写作资源很丰富,社会的变化给作家提供了很多创作空间,年轻作家假如只沉迷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只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jp/8354.html
- 上一篇文章: 7月16日便民信息库免费发布招聘房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