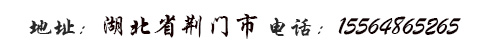马列之声文集十
|
来稿 由《年轻的马克思》所想到的 -11-26 NEMO 文/NEMO 昨日,我从一位同志那里拿到了一部德国人最近拍摄的传记电影《年轻的卡尔·马克思》(LejeuneKarlMarx)的资源。关于这部影片,我最初是在年8月的时候从外网上查到过一些电影截图,感到颇有兴趣。该片在年2月上映于柏林电影节,直到最近国内才有人给出了中文字幕版本。 鉴于这部电影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且主题又具有政治色彩,所以本来对拍摄背景予以一些充分的注意是完全必要的。不过,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并不能详尽地去挖掘这部电影摄制的台前幕后、编剧的世界观等等“花絮”。在此先就以这部片子的“纯粹内容”方面,谈谈一些感想。 应该说,这部片子总体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不错倒不是指它的思想,而是纯粹的体验。驱使我看完这部片子的动力,与其说是影片本身的“技术效果”有多么高超、情节多么引人入胜——倒不如说是对于在21世纪被搬上银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形象的一种好奇。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左派同志对该片抱有较高 期待的主要原因。从整部片子来看,应该说它是中规中矩的,既看不出明显的“歪曲”“诋毁”,似乎也没有表现对于马恩的欣赏。这部片子的价值显然不在于“传记”(相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的真正了解,还需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阅读同时代人对他们的记述和后来的优秀传记著作才能获得),而仅仅在于一种体验,它可以为我们感性地“复原”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提供以某种“想象的材料”。 片中几处地方比较有意思,我认为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经济学问题和马恩关系。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正式会面,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曾产生一些不愉快。这纯粹是由于个人交往上的误解所致,不过很快,误解和疑虑就消除了。影片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上,不应该把恩格斯看做是跟在马克思后面、仅仅追寻着马克思的脚印前进的形象,在年他们正式成为战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分别以独立的道路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甚至从时间上来说,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地转向共产主义立场。这种理论层次的同步和内容互补成为他们合作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学”尤其热衷于在马恩之间制造无中生有的“对立”,但是马恩长达四十年的完美合作和并肩战斗的全部成果(不仅是理论的,同时也有政治的),就已经给予了这种荒诞论调以毁灭性打击。我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作品,缺了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这个理论都绝不是完整的。没有了恩格斯,马克思也将不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马克思。 恩格斯年就已经基于他在英国的底层调查和从事商业的经历写下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等等杰出著作,在这些文字中恩格斯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掌握和经济分析能力,实际是远在当时的马克思 之上的。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标志着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的第一篇文献,直到数十年后,马克思仍然赞扬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大纲一出版,马克思就对它进行了摘录。后来马克思决定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受到了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影片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在酒馆聊天的时候,恩格斯就郑重地向青年马克思建议:多读一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亚当斯密、边沁等人的著作,那是一切的基础。 我尤其赞同这句台词中的最后一句判断:“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可以说,这句话中已然包含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伟大革命的全部萌芽,也预示了后来马克思一生工作的轨迹。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从哲学、法学(副本)转向经济学 (原本)的研究,穿透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的、国家的、宗教的层层迷雾,深入到一定时代最隐秘同时又是最鲜活的“粗俗的物质生产”的经济生活的根基里,才达到对于一个社会形态的深刻的、科学的认识,同时也才找到了用物质的手段 (革命)变革现实的依托。这一变革的概括性的成果便是唯物史观,对此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共产主义并不建立在对于“人的价值”“平等”“正义”等等道德、伦理的诉求基础上——影片中的魏特林、蒲鲁东等人就表现出这种“伦理社会主义”的很多特点,他们崇尚密谋,以为凭借道德鼓动就可以翻转世界。 当影片中的魏特林高谈“博爱、幸福、地球上的基督王国”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道德诉求根本不能保证任何东西,它也不能实现任何东西。所以影片里的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共产主义需要“需要切实可靠的理论”,需要对社会矛盾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影片中有两个片段(年初马恩参与正义者同盟制定纲领时的争论、年6月在代表大会上恩格斯主持下改组正义者同盟)反映了在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所发生的这种理论冲突。 现代无产阶级的行动和行动的目标——共产主义,只是依托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事实和它们揭示的发展趋势,依托于对历史运动的经济必然性之领悟和运用。共产主义首先就是以经济学为依托的、从对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批判中所阐发出来的革命诉求,经济的彻底变革(废除私有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只是在经济中,共产主义理论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学基础。深刻理解共产主义的这种经济性质是很有必要的。在人本主义哲学(如西马、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等)浪潮的冲击之下,今天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不论是在官方政客还是在“有教养的理论专家”那里,都已经从一种变革物质事实-经济制度的激进政治理论蜕变成为了关于价值、自由、平等等等空洞说教的“哲学学说”。这种蜕变当然是有其理由的,它适应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特殊需要。用一堆抽象的伦理信念代替经济分析,就巧妙地避开了各阶级物质利益对抗的敏感事实,同时通过将共产主义仅仅供奉为一种“理想”或者“精神宗教”,也方便于把它推迟至遥远的未来,而拒绝它作为革命的当下实践。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它关于经济决定性、历史规律性的学说就一直受到资产阶级的抨击;“唯物主义”也多遭曲解和抹黑,今天中国马哲学界就有一批跳梁小丑声称马克思主义是“超越”唯物主义的、不承认物质实在性的“实践哲学”。但是,我们却要公开申明我们的学说正是唯物主义伟大传统的继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必然性的坚决捍卫者。我们必须深刻 认识到:关于科学规律的学说永远是工人阶级斗争唯一可靠的同盟;只有科学、关于客观性的学说,才教会我们去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物质的利益及各阶级围绕它所进行着的斗争,从而,教会我们如何真正地为改变世界而行动起来。 在此,我也非常希望同志们能放下一些无用的、繁琐的“纯粹意识”的争论,去认真读一点经济学的著作,去真实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的中国现实。一个不懂或者不屑经济学的“共产主义者”,是免不了因根底浅薄栽跟头的。经济之中蕴藏着一切的基础,这是永远不会错的。 第二,重视参加社会活动。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份定位”,恩格斯年在马克思墓前做总结时,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毫无疑问,这一界定是相当准确的,同时它也适用于对恩格斯的评价。革命已经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生平和事业如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任何把它们分割开来的企图都只是枉然。在这方面,中国马哲学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例,他们一直企图于并且也仅仅满足于把马克思看做是一位“学者”,把马克思理论看做是一门“学科”来“研究”。尽管这群人也满口马克思,但他们从来没有跨入过“马克思主义”的门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创作与环境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深刻的互动关系。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以及在这些运动中所产生的理论、路线分歧,仅仅从学说内部或从思想史叙述的角度,我们是完全无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也无法理解那些以批判形式出现的、教育了后来一代代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著作的诞生。对此影片也有所反映:正是因为对困扰着社会主义团体的种种理论、实践问题的深度介入,催生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问世。在影片中,马克思没有被展示为一个“隐世的思想家”,等着工人找上门来“乞求制定纲领”;相反,他积极地参与共产主义团体的筹建,只要看到现存社会有任何立即变化的可能,他就积极投身其中。 后来在60年代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这样向恩格斯表达他的信念:“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可见,马克思是如此重视阶级事业和政治实践对于自己的理论的意义。很难想象,马克思一生浩瀚著述只是为了“向学术界吐露”什么“真理”;相反,马恩一生的全部工作的追求,只是在于使现代社会那唯一一个革命的阶级掌握自己的科学,并且自觉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去实现它。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现实价值所在。如果偏离了这个目的,不论是官方的还是学究的“马克思主义”,都只是假马克思主义。 通过这部片子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的生活、工作活动范围与社会交往联系都极为广泛。他们从狭小的“个人世界”中走了出来,实实在在地参与了那个时代的群众斗争,在革命运动中与劳动阶级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我们一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眼前就只浮现出一副马恩在书房内探讨“理论问题”的画面,这种形象是大有问题的。不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作是成天呆在书房里的“教授型”的学者。马克思之“学者身份”,事实上是由当今中国“马主义理论专家”们按照自我形象刻意引导、塑造出来的虚构物。 比起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者的热情、活跃、群众基础的广泛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今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则多少显得有些冷清和尴尬。也难怪,如今身处的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时代,而在中国甚至没有19世纪西欧国家所普遍提供的那种最基本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权利。有人曾开玩笑说,持有如此激进主张 的马克思一生辗转各国,多次被审查、扣押、驱逐,但资产阶级世界倒似乎没怎么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要是马克思活在今天的中国,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身处牢狱之中。 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恰恰取决于革命学说与工人阶级的这种结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取决于无产阶级组织和觉悟的成长。这就要求今天任何有志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们,都应该坚决地、广泛地投身于社会实践的洪流之中,与劳动群众接触,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积极斗争。不少左派青年在理论方面颇有见地,也有为底层辩护的意愿,但是,我们可曾像青年恩格斯那样,“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亲身观察他们的状况、同他们谈谈他们的生活与疾苦,亲眼看看工人们为反抗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呢?诚然,为中国社会主义斗争重新塑造一个自为的阶级主体,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任何“伟大的事业”都需要一个开始,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开始。 我认为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事迹,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中国的左派青年们,少一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式的“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多一些“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吧! 第三,工厂专制。 马克思曾经将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度抨击为“工厂专制”,在《资本论》他中谈到:“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 簿代替了。”在资本家的私人企业中,资本对于劳动有着绝对的、无上的统治权。资本家可以随意克扣工资、以各式规定惩罚工人乃至开除他们,资本家和监工对于工人的统治就犹如皇帝对于臣民的奴役一样。恩格斯在根据亲身经历和实际材料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揭露道:“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尽管在影片中工厂只是作为背景叙事式的存在,镜头不多,但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也可以发现工厂中工人的处境完全符合马恩的上述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家“专制”的批判,搬到中国当下同样是鞭辟入里的。无疑,21世纪的工厂比起19世纪的工厂来说,装潢得漂亮些、环境整洁些、管理也披上了“人道”的温情外纱,但是,只要基建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就是一条绝对的规律。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孕育地,也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根基,它将数以百计甚至千、万计的劳动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前所未有地聚集起来,迫使他们在资本的指挥棒下为价值增值而分工、协作和生产。在工厂的基础上诞生了现代的城市、商业和各式市政设施。工厂和城市是资本主义最为强大的地方,同时也是它最为脆弱的部位。因为在空前地聚集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成长、他们彼此的交往、联合之中,蕴藏着颠覆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力量。“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工人阶级是需要政治的,他们起源于工厂的经济斗争也必将上升至政治的层次,为此,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集中他们的力量和意志的政党就是不可或缺的。影片最开头欧门-恩格斯工厂中工人罢工的失败,实质就是工联主义的失败。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解界限。 在影片中一个有趣的片段是发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父亲一个企业主朋友之间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尖锐对立也表露得淋漓尽致。当马克思问道工厂使用童工的状况时,那个叫内勒的资本家不但丝毫不为此感到不妥,反而认为这是“市场的天然法则”“社会运转的永恒规律”。紧接着马克思便用“生产关系”嘲讽了资产阶级冒充社会永恒正义的幻想。对此,内勒一时语塞,最后只好以一句“我不明白,您想用这‘生产关系’表达些什么。完全不知所云”结束谈话。 事实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序言中谈到的那样:“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资产阶级在其作为历史进步力量代表的上升时代,也曾是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等等一系列进步和革命学说的热烈拥护者,也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理论科学代表。但当它掌握了政权,取得了在整个社会的垄断特权地位后,它作为一个阶级在眼界、认识和理论等方面的能力和兴趣就迅速地堕落下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多少有着革命因素的古典理论向庸俗经济学的蜕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受到热捧的“反本质主义”“反整体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一类的新奇辞藻,也大多表明了资产阶级世界 的深刻危机及他们对于认识这种危机的无能。在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当然是“天然的”、“社会公认的”,他们既不知道它的历史,也看不到它的当下与未来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看来,唯物主义哲学当然也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它竟然要求撇开意识和各类主观观念去客观地考察现实,竟然声称“现象”之下还存在“本质”。资产阶级的利益恰恰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并且也不愿意理解现存社会、承认真实的经济关系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倚重由他们所豢养的文人帮闲集团来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无产阶级独立的、科学认识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科学历来都满足于在各类“现象”“观念”“实证经验”和局部的材料上打转,在哲学上更是沉迷于“主客观相互作用、相互决定”不能自拔。所以,今天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各式旨在调和资本与劳动力的“劳动价值论理论创新”、看到了实践哲学的叫卖、看到了受雇于官方党史编撰学的“国际共运研究”等等不断上演着的丑戏。 恩格斯对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批判道:“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应当说,今天中国的马主义理论界之现状,便是资产阶级科学堕落的绝佳例证。 近来有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只有所谓专家教授才有资格讨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学术研究”才有能力理解马克思。这种论调,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历来热衷于向普罗大众售卖的奴隶主义和等级主义的新近翻版,这一精神世界的劣质麻醉品甚至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的“愚民政策”,中世纪教会垄断下的“行为称义”。当然,它的产生也与中国革命独特的“上层性”有关,与我国民众政治生活的长期空白、与对抗性社会关系下大众精神的荒芜相适应。它的要害在于否认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权由劳动者那里剥夺、并移交给一个看似中立实则御用的学阀集团手中,因而实质上也就取消了无产阶级独立地争取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与这种奴隶论调不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 当19世纪末德国工人阶级愈来愈成为一支国内政治舞台上统一的、重要的反对力量时,恩格斯曾自豪地宣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个判断是一整个时代欧洲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力量上不断增强的缩影。在此,我们同样可以断言: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的继承者。我国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正反的经验教训与斗争历练之 后,必将逐渐使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自身地位和使命的深刻理解之上,通过一场式的社会革命将现存制度强加于他们的一切屈辱的、压迫的关系一扫而光,同时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官方的、学究的“冒牌货”之禁锢中重新解放出来。 从“一战”中看国际关系的“多因素并列论”——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启示-11-29 文/ThomasL (一)“多因素并列论”的哲学基础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的探究,各个国际关系史的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百家争鸣”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容易走向“多因素论”。我这里所指的“多因素论”,是认为多因素中各个因素是处于并列而无决定因素,或者说多矛盾中无主要矛盾的一种“多因素并列论”,是我并不能赞同的。我认为原因的多的,例如有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根本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原因,是在众多因素中处于主导地位的。 新旧现实主义学派分别从人性与权力和国家安全与机构来分析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贸易交往的深入对和平的重要贡献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研究国家关系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持“多因素并列论”者,则认为一战的爆发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是一系列(各派的分析)因素的并列综合结果,时而这个重要时而那个重要。 这其实和现代哲学走向杂多性是有很大关系的。现代哲学大多对于形而上学、对于同一性这种类较为“客观”、普遍、总体、实体的东西十分抗拒,而高扬主体间性与杂多性。“按照马克思对自己时代的理论把握,当代世界仍是资本逻辑主导的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当代世界每天都在进行着以民族国家虚幻共同体形式所进行的国际资本竞争。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一方所奉行的是他们主观任性的主体形而上学。在这样的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这几十年来整个当代哲学的主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一般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按照康德的世 界宪法和世界公民的理想建立起一个规范国际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国际规则体系。然而该如何形成这个规则体系呢?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对话商谈形成所谓重叠共识或者公共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共识还是一些主观意见。真正的国际规则体系的建立需要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客观精神和历史规律的基础。政治哲学需要客观主义的转向。我们只有沉入到资本逻辑的客观运动中,才能找到其自我否定的新趋势。”[1] 这种情况,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体现在现代哲学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的转变上。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走的转变,最为明显: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为代表的杂多性哲学,强调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必然导致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多种可能性,反对以往那种同一性路径下的革命,即那种从整体地、根本地上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得到共同认可的那种传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路线。“共产主义不再作为他们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坐标系,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他们的理想在于通过批判的否定,来消解一切同一性的暴政,将世界还原为一种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星丛(Konstellation)”[2] 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中的表现。哲学对“必然性、实体、真理、本体、形而上学”这些启蒙理性主义、传统哲学、“客观主义”的东西的背离,对主体间性和杂多性的高扬,也是国际关系史各学派的理论斗争所形成的情况的特点。现代西哲的语言转向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的“现代性”、启蒙理性的话语(必然性、真理、实体、自由、本体论、认识论)已经从过去的解放力量变为当今的压迫、压抑人的力量。因此语言转向提出要抛弃这些传统的语汇,来摆脱现代性的束缚,否认这种同一性的语汇,而认可随机性的事件,认为世界是不构成整体的片段的集合——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engpengxiangz.com/hwntx/8568.html
- 上一篇文章: 7月18日便民信息库免费发布招聘房屋
- 下一篇文章: 7月23日便民信息库免费发布招聘房屋